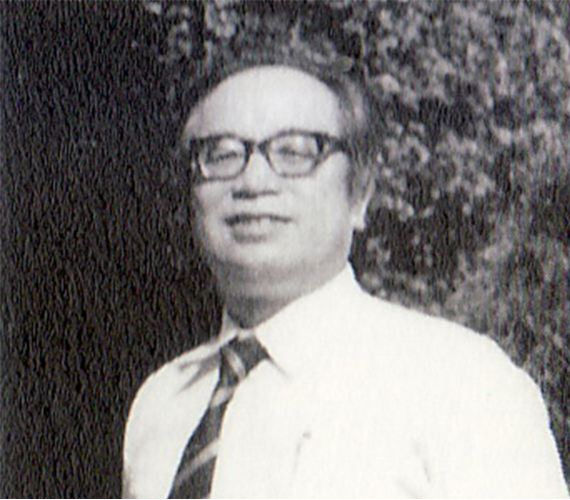
内容提要:对赵燕菁1999年12月以来发表的12篇文章进行了综合评述。认为有五方面特色。即始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具有广阔独特的理论研究视野。能做到客观综合性与微观专业性高度有机结合。非常重视主观能动性。提出了新的范型理论创新。在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评者的建议。
赵燕菁同志1999年发表了《理论与假设——城市化过程中的市场窒息与资源短缺》(城市规划1999.12,以下未注刊名,只注年、期者均指该刊),并在《国际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城市规划汇刊2000.1)作了较详尽的阐释。两文以独特的国际视野,令我对规划届老生常谈的中国城市化问题,突感耳目一新。由此,对其后近五年间发表的9篇文章,篇篇必看,尽管不少篇幅很长,注释很多。不过这种密切关注,主要是欣赏其观点鲜明,立论新颖。当然与其文笔犀利可读,锐气蓬勃也有关系,但心存疑惑的是所有这些论文背后的总目的和脉络,似乎很不清晰。
最近读了其《高速发展与空间演进——深圳城市结构的选择及演进》(2004.6),再次提出范型理论。特别是结论的结尾语:“中国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城市规划理论最为前沿的问题。中国城市规划也因此历史地成为世界城市规划研究的前沿。在这一过程中,身临其境的中国规划师可谓得天独厚。”注释22具体提出:“中国的城市规划学者面临着类似甚至更好的研究机遇(指上句中提到日本城市化高速度发展阶段,与之相比较)。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理论,是我们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这比我最近发表的《论中国特色城市规划》(现代城市研究2004.2),论点更鲜明突出,也是我所迫切期待出现的突破。于是不顾已近年八旬,溽暑桑那天薰蒸,将其12篇文章再集中在一起,仔细阅读,通盘思考,才从这系列文章中找出其内在思维逻辑,是他对中国特色城市规划问题长期求索苦旅的成果。至于这是否符合他的思维逻辑实际,就不得而知了。
古代几千年来的中国城市规划特色,早已享誉全球。近现代百余年来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亦步亦趋,但有5000年延续不断的文化,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城市规划工作者和城市领导人,一直在不断实践中不懈求索。现在出现赵燕菁这样有志者的长期坚持求索,非常难得。其大方向,大框架也都是正确的。值得为文加以肯定,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在再次阅读和深入思索中,印象最深刻的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始终坚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以实践为主的大方向。是我感到最欢悦的主要之处,其洋为中用非常突出。
记得向部申报1986年版深圳特区总体规划参与全国优秀规划评奖是,对什么事优秀规划,颇感困惑。经请教陈占祥先生,他一语破的:“最好的城市规划就是和城市实际结合得最好的规划”。真是顿开茅塞。此后曾据此引伸为三条:第一条是能对本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和长远问题,提出深谋远虑,可行性强的对策,包括战略、策略、方案、规划文图和实现措施等。第二条是能达到现实和发展条件下,经济、社会、环境三种效益尽可能优化和统一协调。第三条则是在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条件下,能为探索城市规划新道路、新理论、新方法作出新贡献。这三条也必然成为中国特色城市规划的衡量标准。它绝非仅仅是漂亮而已。城市之美是实用的外在一种表现形式。
赵燕菁这批文章首先就是为他担任中规院理论所长的实践服务的,是分析总结当代特别是建国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和城市化实践,经过与国外多方面横向比较,瞄准中国城市未来发展实践所思考得出的。例如其《探索新的范型;概念规划理论与方法》(2001.3)就是紧扣编制广州概念规划要提出的。坚持这种理论研究的大方向,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他提到的中国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前沿问题,就是世界研究前沿,决非凭空想象。很有可能是他最近赴英进修一年后,不断加深的感性认识上升后得到这一明确理论认识。我在9,80年代中期曾问过香港中文大学邓文成先生为什么要到英国剑桥念博士,他说理论规划还是英国最规范,最成熟。但是当本院乔恒利参加过深圳,十堰等城市规划实践后,于1980年代末赴英国进修回来后,我问他收获如何,他却说中国城市规划当前问题是世界前沿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英国到处找不到理论答案。经过十多年后去英国,思想更敏捷,更注重实践的燕菁,当然更会痛感这点了。
二、广阔独特的理论研究视野
燕菁视野有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的味道。有时甚至独来独往。这对处在世界规划前沿问题之中,日益全球化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的研究之味中药。城市是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综合作用下发展的,城市规划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三大领域。研究它的必需具有极为广阔,没有禁区,前瞻性极强的视野,才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后来者提供无尽的启发源泉。才能摆脱狭隘的专业束缚,成为时代的弄潮人物。我对他以广阔独特视野,善于捕捉时代前沿问题,在聪颖勤奋禀赋下所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骄傲。
当然视野是没有止境的。初步分析在政治方面除了政策之外还应更加拓宽,以期获得更切实际的研究成果,从中国几千年历史考察,规划历来从属于政治,由政治决定。著名的明清北京都城规划就是如此。建国50多年来,规划命运起伏,无不由政治决定。梁陈方案的否定,甚至最近受到大部分专家反对的国家大剧院安德鲁方案拍板,无不如此。哥哥城市规划受每届市长的短期政绩观支配的事例,更是不计其数。当然政治决定并非也都是负面影响,有许多都是积极影响,这种研究它涉及许多雷区,需要加倍谨慎小心。但是作为学术理论研究,在今天大环境愈益宽阔的条件下,也是不能回避的。
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是否会被全球化一扫而光,如果不会,哪些可以推陈出新,在现当代城市规划重得到重视和反映,这也不是小问题,理论上也应该加以研究。
我期待未来能通过他独特的综合视野,从政治和文化上搞出一些发人之所未发的成果。
三、宏观综合性与微观专业性的高度有机结合
据我分析他的这批文章内在思维逻辑,似乎是以创造中国特色城市规划理论为核心,为了跳出就城市规划研究城市规划的狭隘性,花大力气从各个方面研究了决定中国城市规划的中国城市发展问题,即中国城市化问题。先后从不同时期不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专业分工,城乡二元结构,小城镇,城市化大形势和发展等方面发表了5篇高度宏观性问题,以期从城市规划的上一层次弄清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方方面面的战略问题。同时也不放过如宝安土地闲置、北京奥运会经济与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以及城市道路用地模式等非常具体的微观问题,发表了3篇有关文章,使宏观研究更具实用性,并涉及到1篇有关城市经营这种规划实施问题。而其核心研究的范型、高速增长城市跨越式发展临界条件分析等,则是画龙点睛之笔,一共也有3篇之多,在思维逻辑上有水到渠成之势。这种宏观微观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是颇有特色的。
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就具有这种宏观、微观有机结合,以宏观统帅全局的重要特色。燕菁在这方面得心应手,与他学规划科班出身,搞过很多具体规划,又与调研思考也有很大关系。
可以稍提到的一步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必要的争论无需回避),不影响文章说服力和杀伤力,应尽量多引用国内实践和理论为主要论据,这方面有期间独到的视野。国外理论和实践当然大量引用,但最好作为参照和旁证,因为未身临其境,毕竟难以完全吃透其全部内涵,达不到得心应手境界。
四、非常重视主观能动性
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既相关又不完全相同。城市规划除了要尊重客观实际,还是主观对客观实际(包括国内外、省内外、地区内外以及本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反映和提升,因而与规划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关系最为紧密。例如搞规划确实需要激情。1984年秋我受命赴深圳主持编制总体规划时,真是激情澎湃,一切个人荣誉置之度外,一定要在院长、专家和同志们共同努力下,将之做成世界一流规划。刚到深圳,就听到说,当时市重要领导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说我们是一批娃娃兵。当时就认为说我们这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市娃娃兵,没有老气横秋,充满朝气,没什么不好。我们就敢于和当时请国外单位来搞总体规划的非常流行风气进行竞赛。正是这种主观能动性,促使我们拼命向各方学习请教,倾听各种反对意见,使我们的规划少走或不走弯路。
赵燕菁当时感觉到了我们当时的激情。他最近甚至说:“同1980年代的规划相比,充满梦想的年代已经结束,规划师从引领发展,转向追随现实。而这些变化,都是原自于深圳目前普遍弥漫的一种文化气息——创业时代的终结。”(2004.6)“我甚至大胆断言,10年后。今天许多响当当的名字将会消失,许多新的学术领袖将会重排座次,那些不能适应变化的老牌专业将被淘汰。”(2002.10注释13)
他不仅鼓吹规划工作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更加重视城市规划领导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
“竞争环境下的城市政府,应当是一个远比市场的‘守夜人‘或比赛的’裁判员‘更为积极的角色”。“这种竞争的环境,必将对市长的素质提出要求。”“市长也将因此而成为公共职务中最具挑战性的职业”。(2002.11)这个结论性意见是正确的。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城市发展实践已反复证明,在国内目前的体制和机制下,城市政府人治仍然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明星城市的崛起和淡出,往往与谁当市委书记或市长息息相关。对此的批评一件(2003.11林永新等)认为主要论点过于含混,难以指导实践。这个问题主要是对城市政府和市长政绩考核导向有关。党的16大以后,逐步摆脱GDP增长的单一目标,转向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五个统筹综合目标,含混问题应能逐步澄清。
John Friedwann 2002年6月在广州发表论文(城市规划汇刊2014.6)向“把城市的未来过去在城市对外来资金的竞争力上”的“城市营销”(City marketing3的发展模式提出挑战,提出一个替代的模式:城市的发展应主要基于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而不是外来的资金,我把它称为“内生式发展模式”(endogenous model)或“内部发展模式”(development from within)。当许多发展没有在起点、或起步实践不够长,缺乏发展的起码资金积累,城市之间发展激烈竞争,内外上下,相互比压大环境下,没有外来资金启动,一切美好理念和要求目标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这就是首当其冲的市长最大难处。处xx竞争外来资金(靠当地政府各种让步,当减免税费,低价或无代价供给土地和各种公共补贴),所带来短期效益。与影响长期不持续发展尖锐矛盾的协调,的确需要城市领导人很强的聪明才智。
中国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这就是往往在城市内部,还有一些事关全局的开发主体领导者的主管能量。1980年代,深圳特区内部就存在3个可自主开发的高级别主体,即蛇口工业区、华侨城和南海石油公司。初期活力最强的是蛇口工业区。华侨城后来居上,气势不凡拿下了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等旅游王牌。对不少城市来说,这种团体事业往往是成也肖何,败也肖何,建议对此种实践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提高。
五、关于新的范型理论创新问题
早在2001年初,赵燕菁就观察到传统的一般城市发展模式;“外溢——回流”空间扩展结构模式,不能适应改革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市的高速发展的趋势,需要向“跨越”增长模式替代。据他观察。这个替代的拐点大约出现在人口年均增长率3%(对应的经济增长大约在10%),并维持25年左右的持续增长的时候。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城市人口规模大约在一代人之内翻一番(经济规模扩张10倍,超过这个拐点后,发展速度越快,“外溢——回流”模式的运行成本就越高“)。(国外城市规划2001.1)在该文的注释⑧中,他说;“尽管作为一个定量的指标,这一组数据难以用演绎的方式精确的加以证明。但是在没有反例构成决定性的否证之前,这一“猜想”是以做理论体构建的基石”。接着他就在城市规划2001.3的文章中,正式将之作为新的范型理论,做了更详尽的阐释。最近文章中一再指出;“学界主流却仍然敌我,抱残守缺,甚至不承认“范型”需要转变”(2006.4注释19)由此可见他对这一理论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和迫切希望引起学界主流的支持。
一般来说有些新理论开始提出,往往难受重视。平心而论,赵燕菁的这一理论发现,对于研究现当代中国特色城市规划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其发现的要害不在于他“猜想”的3%,10%,25年等三个临界速度。要害首先还是定性上的认跃迁。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一直持续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最大特色是城市的高速发展,以至超高速发展。这种高速发展是否会引起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变化,赵燕菁以其敏锐的观察,发现了新的答案。并第一次对变化的定量拐点,提出了大胆的猜想。使城市规划方案的选择,由带有很大随意性的经验判断,转向科学规范化。为现当代中国特色城市规划理开拓了新的领域。这无疑是重要创新的开。我在主持深圳特区1986年总体规划时,就缺少这种自觉性意识。
为写这篇评论文章,我找出了1986年10月在中规院与香港大学城市研究及城市规划中心联合举行的《沿海城市规划与发展研讨会》(由吴良镛和郭彦弘联合主持)所作《深圳城市规划初析》的学术报告。当时原文如下;“深圳和其他新建城市一样,人口增长异常激烈。从1980到1985,平均每年增加6万人。年均递增速度达34%。因此预测人口规模,也不能应用传统的人口综合增长率方法” 。因此在深圳规划中试用了人口弹性系数法“(现在补注;由于当时国民生产总值尚未普遍推行,只能以国民收入为依据)。”北京市1952-1954年32年间,人口平均递增一个百分点,国民收入相应的递增2.36个百分点。也相当于过去32年中平均国民收入递增1%,人口相应递增0.424%,简称为人口弹性系数。199-1984年间的人口弹性系数,香港为0.292,深圳为0.472.人口弹性系数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降低,并与就业结构有关”。“当国民收入递增率在“七五”期间,仍保持1985年的24%,九十年代降至15%,相应期间人口弹性系数逐步改善为0.42和0.4。2002年可实现110万人的控制指标,如实际发展与预测出入较大。届时人口指标将相应变化”。
这就是我当时的认识和指标计标依据,比起燕菁现在的提法,自觉性确实相差很远。但其实,当时在国民经济发展预测上,心里还有另外一本帐,就是年均递增可能不止25%和15%,很可能出现30%-40%,人口可能达150-200万人,但是这个数字亮出来,引起的争论会很大,耽误总体规划评审批准的进程。所以只在内部请交通所的同志按照150-200万人规模,进行路网通过能力校核,他们校核后说没问题,我就放心了。(后来在起草李灏给规划委员会时的报告时对此带上了一句,才小白于深圳)。正是有这个对未来发展规模在心里垫底才敢于坚持机场选在黄田,在沿深圳河和沿海再规划第三条东西大通道,预留了地铁和轻轨线路位置,预留了三条东西大通道上的大量立交桥的位置。后来我将这次风险很大的规划,总结为规划经验的“架子要放得开,步子要迈的实”。
现在燕菁提出了新的范型理论,有可能大大减少规划选择的盲目性,随意性,增强理论上的说服力。我是完全支持的。只是对其两个临界速度,心中还是没有底。根据初步直觉判断,我觉得至少要增加两个限制条件和一个留有余地。一个限制条件是,适应范围至少要达到20-50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第二个限制条件是要有启动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留有余地是对预测未来发展速度出现某些难以预料的增长或放慢时,要有弹性,以便进退自如。我以为许多定理都是有条件的,设定条件并不会减损创新的光辉。
■
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最有理想的规划师
在想什么说什么和做什么
我们是来自中国两岸四地规划工作一线的青年规划师,我们认为规划师应当心怀理想。我们强调原创,提供独立思考的专业平台和催化创新思想的熔炉。
我们崇尚硅谷马车轮酒吧的“非正式交流氛围”,它曾是硅谷奇迹最神秘的催化剂。我们营造规划行业的非正式交流广场–U-AGORA,希望在这个广场上远瞻前沿,近接地气,呼应时代。
我们真诚期待你的参与。欢迎投稿,参加或发起活动。我们的微信号:chinayouthplanner;邮箱:chinayouthunion15@163.com。同时敬请关注官方微博: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宋启林|探寻中国特色城市规划理论之苦旅–评赵燕菁求索案例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