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在知网发布,识别下方二维码 或 点击文尾“阅读原文”即可下载阅读全文

精彩导读
土地发展权是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贯穿“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实施和管理全过程。现代意义的土地发展权概念最早起源于1947年英国的《城乡规划法》。该法案出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大规模城市建设和都市区扩张的背景下,目的是在保护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基于公共利益对土地开发的内容、强度及开发权益的转移进行规制。其后几十年间,欧洲、北美及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相继建立了类似的土地发展权制度体系[1]。
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针对土地发展权概念开展了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领域:其一,是关于土地发展权的内涵,既包括土地用途转变的权利(如农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转变)[2-3],也包括土地开发强度的改变(如容积率提升)[4]。其二,是土地发展权流转的效应研究,如以折抵指标为核心的浙江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5-6],以及通过对重庆地票制度分析发现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发展权交易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7]。其三,是土地发展权转移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机制研究,特别是农村土地向城市建设用地转变过程中的利益博弈[8-9]。总的来说,上述研究主要关注在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土地从农业、农村用途向城市建设用途转变过程中,地方政府与社会(村集体、村民)和市场(企业)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土地发展权受到政府内部治理架构调整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新的空间治理体系更加强调理顺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事权关系,中央政府强调战略指引、底线管控与局部聚焦,地方政府关注要素配置、增质提效与权益协调[10]。另一方面,进一步强调以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空间形态[11]。特别是在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间的协调和博弈趋势日益增强[12-13]。因此,区域治理框架下的垂直和水平重构趋势都显著增强。而土地发展权在区域治理重构,特别是府际关系调整的背景下,呈现出新的内涵、特征和演化机制。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分析了区域一体化下土地发展权的空间重构过程与内在机制,以丰富城市区域化背景下土地发展权的流动机制,加深了解中国以土地为中心的发展模式(land-centric developmental mode)的政治经济内涵。
中国近40年的城镇化进程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资本积累与空间重构的过程。土地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是解释中国地方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模式[14-15]。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使得土地可以作为重要的发展资源为地方政府所使用[16]。地方政府依托严格的土地市场管制,以土地征收的模式实现土地商品化(land commodification)[17]。一方面,通过土地征收价格与土地拍卖价格的价格差,获取可观的土地出让金收益;另一方面,通过高价出售商住用地、低价出售工业用地的方式,既获得土地资源带来的直接出让金,又可获取相关的税收收益[18]。进而,以土地财政的方式将城市发展的多要素(如产业、基础设施、住房、公共服务、税费等)相互捆绑,形成“以地生财,以财养地”的中国城市发展的制度基础[19]。土地财政系统中,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土地实际所有者将土地作为城市资产通过土地租赁等方式吸引外来投资,为城市发展积累资本。同时,土地收益直接与政府官员行政绩效挂钩,构成官员晋升的制度激励[20]。丰厚的土地收益和企业税收也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能力[19]。进而地方政府以公共支出的形式通过投资基础设施、科教文卫设施、公共住房等进一步吸引企业与外来劳动力,成为推动城镇化的主导动力[18-19]。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由于通过协议形式低价出售工业用地,往往通过商住用地的高价出售来弥补低廉的工业用地价格造成的亏损[18]。近些年,由于消极的外部经济环境及日趋激烈的住房投机,商住用地更受地方政府青睐,甚至不少挂名产业新城的城市新区沦为房地产新城[21]。
1.2 全球区域治理兴起与中国区域治理实践
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交互影响下产业碎片化和流动性被加强,西方国家二战后盛行的福特—凯恩斯主义逐渐被后福特—新自由主义所取代[24]。一方面,民族国家开始放松管制,实施不均衡的区域政策;另一方面,城市开始个性化发展,逐步摆脱对“国家经济”的附属,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25]。20世纪90年代,一些城市依靠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如国际金融与贸易、保险及银行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跨国企业总部的集聚,形成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城市网络[26]。同时,城市区域化开始出现,当交通成本低于产业在城市内集聚的交易成本时,受规模报酬递减影响,产业资本出现在核心城市外围地区空间集聚的现象[27]。为强化城市区域作为国家间经济竞争的管理单元并提供跨管辖权的公共服务供给,一系列次国家(区域)组织相继成立,构建了稳定的城市区域治理体制[28]。城市区域治理具备3个特征:一是具有稳定的管辖权的区域政府或区域权威组织以实现有效协同与公共服务供给[29-30];二是形成跨界合作网络,即依托不同区域治理事务形成广泛的城市联盟[31];三是大量非公共部门参与到区域治理中,如非政府组织、市民团体、私营企业等,形成多中心治理[32]。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同样建立起以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的国家经济体系,并通过行政分权与分税制改革,确立以土地财政为制度基础的地方经济增长模式[33]。1980年后,借助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制度红利,城市经济出现史无前例的发展,催生出多样化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式,如乡镇企业主导的苏南模式及集体经济主导的佛山模式[34]。城市经济的崛起也带来了产业资本的空间外溢,强化了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12]。与此同时,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发展成为早期的高度城市一体化地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本质是政府主导的行政过程,非政府部门被排除在区域事务的行动框架之外[32]。中国城市区域治理嵌套在现行的政府行政框架之中,表现为纵向的省—市关系与横向的城市间关系[35]。省—市关系核心是上下级政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6];市(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推动城市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构建地方竞争优势[37]。省政府则分配发展任务、协调统筹区域发展、规制地方无序竞争、提供地方发展资源等[38]。其中,土地发展权就是从中央经省向地方层层转包的关键发展资源之一[39]。城市间关系则表现为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变化关系。城市间竞争根植于现行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行政区经济”模式及“松脚型”产业投资模式[18],导致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40-41]。城市间合作的产生是由于城市间不同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发展资源的配置[38]。在不同的区域发展项目中,纵向与横向的行政治理关系演化出不同区域治理模式,如协同型治理与包干型治理[13]。
由此,笔者认为分析区域治理框架如何重塑土地发展权应基于两方面理论认识。首先,地方层面的土地发展权不是孤立和分割的,而是贯穿当地产业、财政和城镇化等多领域的核心资源。这意味着地方政府间以土地发展权为媒介开展合作,会面临复杂的区域协调。其次,政府纵向层级关系上,土地发展权是一种自上而下进行委托代理的资源。省政府虽然不直接使用这种资源,但可以通过对其重新分配,引导土地发展权更好地释放发展效益,实现区域发展目标。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归纳其不同阶段的治理框架特征,对其土地发展权的空间重构机制进行研究,对当前以土地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如何衍生新的制度形态进行系统探索。
深汕特别合作区最早追溯到早期东莞与汕尾合作建设的大朗(海丰)产业转移园,2008年10月由深圳接替东莞,并更名为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园①。因地理条件、招商引资不力等因素致使园区一度发展停滞。为扭转这一局面,广东省委、省政府推动建设深汕特别合作区,合作期限为30年(2011-2040年),并赋予其地级市级别的人事任免权。合作区在原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园基础上建设,地处汕尾最西端,涵盖海丰县下辖的鲘门、小漠、赤石、鹅埠四镇,总面积达468.3km2。
2011-2017年间,合作区采取深圳、汕尾两市分工共管的模式,由深圳负责经济发展(招商引资)与土地开发等,汕尾负责社会服务与土地征收等。至2017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方案的批复》,合作区的建设管理转为由深圳全面主导,成为深圳“第11个区”。合作区进一步配套建设法院与检察院,实行省直管的财政体制②。
本文着重分析深汕特别合作区建立的背景以及至今的多次管理权属调整过程,从区域视角审视土地发展权的权属变化及收益变化。笔者对深汕特别合作区进行了3轮调研:第一轮调研集中在2016年3-4月,重点访谈了5名合作区行政管理人员及4名参与合作区相关规划编制的规划师;第二轮调研集中在2019年2-3月,重点访谈合作区行政管理人员及相关规划编制人员各3名。第三轮调研集中在2020年11-12月, 重点访谈了2名合作区行政管理人员。以深度访谈的方法共计访谈17名合作区相关人员。访谈通过“滚雪球”的方法获取深汕特别合作区利益分配、职权演变及动力机制等内容。同时,系统分析和归纳了合作区发展的空间规划、政府政策与新闻报道。
3.1 汕尾独立运作的土地发展权与社会经济状况
珠三角是土地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下的典型城市区域。自20世纪80年代,依托于不同的地理区位条件、地方文化与社会经济基础,形成了多种城市发展模式,如出口导向型的深圳模式、集体经济主导下的佛山与中山模式、村镇经济主导的东莞模式等[12]。高度碎片化的城市经济体现了珠三角城市不同的土地发展权经营路径。深圳主要借助外资(港资)将征收土地进行非农开发。东莞、佛山等依赖内资(尤其是本地资本)进行土地开发与产业建设。
为支持粤东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并推动珠三角核心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广东省自21世纪初开始推动劳动力与产业“双转移”政策。在广东省的动员下,深圳于2008年接替之前运营效果不佳的东莞与汕尾合作项目——东莞大朗(海丰)产业转移园,成立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园。总面积达1308hm2,位于汕尾的鹅埠镇与东涌镇⑤。该产业园区确立了深圳注入产业,汕尾供应土地及配套各项基础设施的治理模式。该阶段的深汕合作中,汕尾以土地“入股”,供应土地作为发展空间(继续占有土地发展权),同时承担提供基础设施开发的责任;深圳提供产业,利用其自身产业基础和招商能力,动员企业入驻园区。但实际运作中由于汕尾财政能力薄弱、深圳提供的资金有限、原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及合作区位置偏远等因素,园区建设效果不理想,土地价值提升有限。
2011年后,广东省进一步推动产业转移强度,提出“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战略”,将珠三角次级都市圈扩容,汕尾与河源纳入到“深圳-东莞-惠州”都市圈。为此,广东省在区域尺度寻找城市合作的示范项目。与此同时,深圳由于城市建设用地严重不足,产业难以转型升级,也急需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最终,广东省与深圳、汕尾进过多轮协商,决定在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园的基础上建设深汕特别合作区作为区域合作的示范标杆,将海丰县的鲘门镇、小漠镇、赤石镇、鹅埠镇四镇列为合作区范围。这4个镇虽然是汕尾距离深圳最近的地区,但也是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城市建设条件最差的地区。
该阶段主要特征是:深圳以资金入股,既提供招商引资能力,引导企业入驻园区,又提供全部建设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开发与产业扶持;汕尾则以土地入股,提供园区所需土地及配套的社会服务,如征地、水电供应、招工等。同时,省政府在城市间合作治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提供部分建设用地指标、赋予园区地级市一级人事任免权及提供产业扶助资金。
不同于汕尾独立运作土地发展权,合作区的土地发展权来源于省政府与汕尾的共同建构。根据《深汕特别合作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合作区有5174hm2的建设用地指标缺口。规划设想约2000hm2土地指标来源省政府补偿,汕尾提供约2900hm2,通过土地集约利用与围海造陆获得指标约300hm2。实际上汕尾城区提供约200~300hm2,而海丰县仅愿提供100hm2,巨大缺口最终依赖于省政府从计划单列指标中按年予以补偿:其中,2014年提供约70hm2,2015年提供约370hm2。虽然汕尾市以土地入股,但未能提供足够建设用地指标,意味着土地发展权的构建依托区域治理框架由广东省与汕尾市政府合作完成。
区域治理稳定性取决于各方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汕尾市可获得一小部分土地出让金。税收上,省政府从合作区获得一定比例的地方级税收,深圳与汕尾在2015年后获得12.5%的合作区地方级税收,2020年后获得25%的合作区地方级税收⑥。土地发展权产生的土地出让金与地方税收除了留给合作区使用的部分,省政府与地方均能取得可观且平衡的收益。因此,合作区构建了稳定的区域治理结构。虽然深圳以资金注入主导经济发展,享有合作区的土地租赁权与开发权,但实际运作中,尤其是土地征收上仍存在政府协作不利情况,导致合作区发展陷入困境、进展缓慢。
“合作区的领导班子是深圳一半汕尾一半,有一些招商引资,特别是涉及到企业分成与土地征收等,有可能因为各自利益,需要很多协调,效率很低。我了解到合作区在跟海丰县合作时,因为土地征收权在县一级,所以跟海丰县签订了‘征地包干协议’”(访谈者:规划师A,2019年2月)。
“根据发展需要,深圳提出在5年或10年内,需要征多少地,根据地的面积,深圳出钱,但是地怎么征由海丰县负责。就是深圳出钱,海丰出力。但由于海丰县的工作力度,成片征收的难度以及政策实施难度等,一直推进缓慢。因此,一直到大概2015-2016年,合作区整体有些进展,但不是特别显著”(访谈者:规划师B,2019年2月)。
综上,深汕合作模式下深圳以资金与招商能力入股,提供资本用以土地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招商能力引导企业入驻园区。汕尾以土地入股,提供土地使用权,并且与省政府合作建构土地发展权。但由于政府间合作存在协调不力且效率低下问题,合作区发展缓慢。
鉴于深汕合作模式中的困难及投入的大量资金与人力成本,深圳市对合作区进展严重不满。合作区在省政府的协调下,2017年进行了新的体制机制调整,从深汕合作转变为由深圳全面主导。汕尾考虑到四镇之前薄弱的经济基础,因此也同意将合作区交由深圳全面接管。该模式下深圳负责合作区全部日常事务,包括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等。合作区仅在行政版图上属于汕尾,管辖权上完全交由深圳负责。
治理框架上,深圳继续提供发展资金与招商引资能力,土地所有权归汕尾,而土地发展权归深圳。合作区的建设用地指标主要由深圳与广东省共同提供。一部分是源于省政府的预留指标,一部分则来源深圳的建设用地指标。
“今年建设用地指标改革,指标主要从省下达下来。广东省分给全深圳133hm2,而深圳分给合作区的只有26hm2。我们一个项目就用完了。但广东省预留了一部分指标,称为‘民生12类’。涉及到民生项目,如学校、医院,可以额外使用省里面的指标,不用深圳的。我们目前正在做土地报批,预计可以拿到大几十公顷”(访谈者:合作区官员A,2020年11月)。
“去年省里面直接给合作下达指标215hm2,2017-2019年间陆续保障了合作区每年约200hm2的指标。省里面对合作区发展还是非常支持的。此外,深圳有指标也没有地方用了,所以指标也都陆陆续续分给我们,优先保障合作区”(访谈者:合作区官员B,2020年11月)。
第二阶段为深圳汕尾合作开发阶段。该阶段包括前后两个过程,前一过程以深圳提供招商引资为主,并注入少量发展资金;汕尾保留土地所有权与发展权,并承担主要的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责任。但由于汕尾市政府财政资金缺口过大,该阶段区域合作成效不佳,土地价值释放有限。后一过程以合作区成立为标志,深汕合作强度加大。该阶段,深圳主导招商引资并提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等全部资金,汕尾以土地发展权入股,并负责相关社会事务。合作区所属土地的发展权虽然归汕尾市政府所有,但治理框架由汕尾市政府与省政府共同建构。该阶段由于受地方主义影响,地方政府在合作中协调不力且效率低下。
第三阶段为深圳主导开发阶段。该阶段中,深圳提供发展资金、招商引资并获得全部土地发展权及相关收益;汕尾则被排除在合作区治理框架之外,但由于行政区划并未调整,合作区土地名义上仍属汕尾。此外,合作区的土地发展权也得益于广东省对深圳的支持。由此,合作区的行政关系被理顺,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地显著提速,土地价值得到完全释放。
区域治理框架下的土地发展权重构特征包括3方面。首先,区域内不同城市间的发展“落差”具体表现为行政分权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土地发展权使用效能的差异,并成为土地发展权在城市间流动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40余年间,深圳凭借区位优势高效地利用了所辖土地的发展权,同时显著提高了在规划、财政、产业等方面的城市治理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其土地发展权的利用能力。汕尾则恰好相反,土地发展权利用效率不高和城市综合治理能力不足,导致城市发展缺乏动力。所以,当土地发展权受到空间总量约束时,深圳有较强的驱动力寻找区域内其他发展差距较大的地区来拓展发展空间。
其次,当土地发展权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自中央向地方进行委托—代理的过程中,省政府角色具有层级中间性和过渡性特征。一方面,省政府需要落实中央意图,行使管制职责,而很少作为土地发展权的直接使用者;另一方面,相较于中央政府,省政府更为积极和直接地引导地方发展并进行区域协调,而土地发展权是重要的协调工具之一。从深圳在汕尾建设产业转移园到后来建立合作区和管理体制调整,可见省政府在土地发展权方面的权力引导和制度支持。
最后,合作区从建立之初的“共同管理”到现阶段的“完全托管”,仍然回到行政区治理模式。如前所述,深圳和汕尾间的发展“落差”是土地发展权流转、区域合作的动力,但同时两地在利用土地发展权能力方面的显著差距使得合作开发、合作管理效果有待提高。因此,合作区最终被完全托管给深圳市运营,形成了深圳城市扩容的空间结果。从深圳拓展空间发展权以及区域经济总量的提升角度来说,目前的模式的确更为有效;但是,这种模式也会可能导致汕尾难以从合作区的开发建设中获得治理能力的提升。由此可见,土地发展权的空间重构表明虽然发达城市区域(如珠三角)对功能一体化有迫切需求,但有效的省市多元参与和跨区域协同治理在短期内仍面临诸多困难,特别是边缘地区的城市治理能力不足问题。
注释
参考文献
[2] 沈守愚. 论设立农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意义[J]. 中国土地科学,1998,12(1):18-20.
[3] 王小映. 全面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J]. 中国农村经济,2003,19(10):9-16.
[4] 王万茂,臧俊梅. 试析农地发展权的归属问题[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6,23(3):8-11.
[5] 汪晖,陶然. 论土地发展权转移与交易的“浙江模式”——制度起源、操作模式及其重要含义[J]. 管理世界,2009,25(8):39-52.
[6] 张蔚文,李学文,吴宇哲. 基于可转让发展权模式的折抵指标有偿调剂政策分析——一个浙江省的例子[J]. 中国农村经济,2008,24(12):50-61.
[7] 顾汉龙,刘忆莹,王秋兵. 土地发展权交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时空溢出效应——基于重庆地票交易政策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1(3):126-134.
[8] 王永莉. 国内土地发展权研究综述[J]. 中国土地科学,2007,21(3):69-73.
[9] 田莉,姚之浩,郭旭,等. 基于产权重构的土地再开发——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地方实践与启示[J]. 城市规划,2015,39(1):22-29.
[10] 林坚,赵晔. 国家治理、国土空间规划与“央地”协同——兼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演变中的央地关系发展及趋向[J]. 城市规划,2019,43(9):20-23.
[11] 张衔春,许顺才,陈浩,等. 中国城市群制度一体化评估框架构建——基于多层级治理理论[J]. 城市规划,2017,41(8):75-82.
[12] 张衔春,杨宇,单卓然,等. 珠三角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机制研究——基于产业合作项目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比较[J]. 地理研究,2020,39(9):2095-2108.
[13] 张衔春,栾晓帆,李志刚.“城市区域”主义下的中国区域治理模式重构——珠三角城际铁路的实证[J]. 地理研究,2020,39(3):483-494.
[14] LIN G C S,ZHANG A Y. Emerging Spaces of Neoliberal Urbanism in China: Land Commodification,Municipal Finance and Local Economic Growth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J]. Urban Studies,2015 (15):2774-2798.
[15] HE C,ZHOU Y,HUANG Z.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J]. Urban Geography,2016(3):436-457.
[16] 雷潇雨,龚六堂. 基于土地出让的工业化与城镇化[J]. 管理世界,2014,30(9):29-41.
[17] XU J,YEH A G,WU F. Land Commodification:New Land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1990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9(4):890-913.
[18] 陶然,陆曦,苏福兵,等. 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J]. 经济研究,2009,44(7):21-33.
[19] 孙秀林,周飞舟. 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J]. 中国社会科学,2013,34(4):40-59,205.
[20]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2007,42(7):36-50.
[21] 陈浩,王莉莉,张京祥. 国家空间选择性、新城新区的开发及其房地产化——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J]. 人文地理,2018,33(5):63-70.
[22] CHENG Z,WANG H,WANG L,et al. Mix Leading to Success? Explor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in Peri-Urban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18 (82):1-8.
[23] JIAO Y,YU Y. Rising Private City Operato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Study of the CFLD Model[J]. Cities,2020(101):102696.
[25] 马学广,唐承辉. 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下城市群的国家空间选择性研究[J]. 人文地理,2019,34(2):105-115.
[26] 马学广,李贵才. 西方城市网络研究进展和应用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2012,34(4):65-70,101.
[27] SCOTT J.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ity-Region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01(7):813-826.
[28] 殷洁,罗小龙. 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城市与区域重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人文地理,2013,28(2):67-73.
[29] 洪世键. 大都市区政治碎化与中国的大都市区治理改革[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1):50-59.
[30] 张衔春,赵勇健,单卓然,等. 比较视野下的大都市区治理:概念辨析、理论演进与研究进展[J]. 经济地理,2015,35(7):6-13.
[31] 洪世键,张京祥. 中国大都市区管治:现状、问题与建议[J]. 经济地理,2009,29(11):1816-1821.
[32] 张衔春,单卓然,许顺才,等. 内涵·模式·价值:中西方城市治理研究回顾、对比与展望[J]. 城市发展研究,2016,23(2):84-90,104.
[33] 牟燕,钱忠好. 破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困境的路径选择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2015,29(12):18-25.
[34] 曾刚,尚勇敏,司月芳.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演化——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J]. 地理研究,2015,34(11):2005-2020.
[35] 罗小龙,沈建法. 长江三角洲城市合作模式及其理论框架分析[J]. 地理学报,2007,62(2):115-126.
[36] XU J,YEH A G. Interjurisdict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Bargaining: The Case of the Guangzhou-Zhuhai Railwa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China[J]. China Quarterly, 2013(213):130-151.
[37] 孟卫东. 论责任政府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 管理世界,2008,24(7):172-173.
[39] 林坚,许超诣. 土地发展权、空间管制与规划协同[J]. 城市规划,2014,38(1):26-34.
[40] 周琳,范建双,虞晓芬. 政府间竞争影响城市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双边效应研究:基于财政竞争和引资竞争的不同作用[J]. 中国土地科学,2019,33(5):60-68.
[41] 沈坤荣,付文林. 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J]. 经济研究,2006,41(6):1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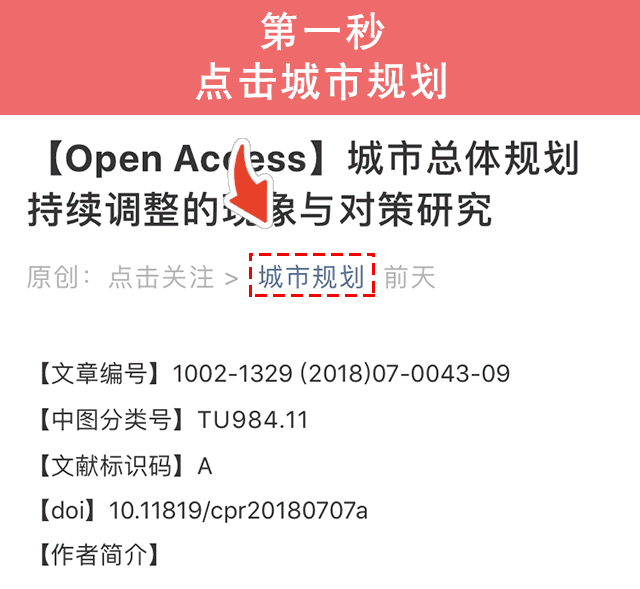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Open Access】区域治理框架下的土地发展权空间重构研究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