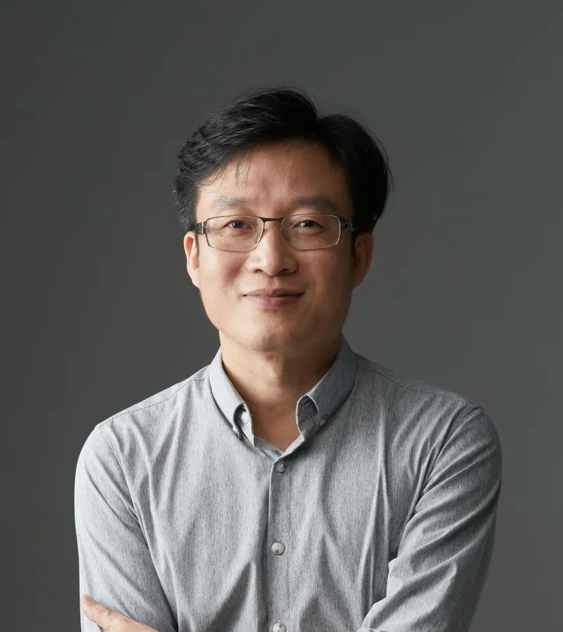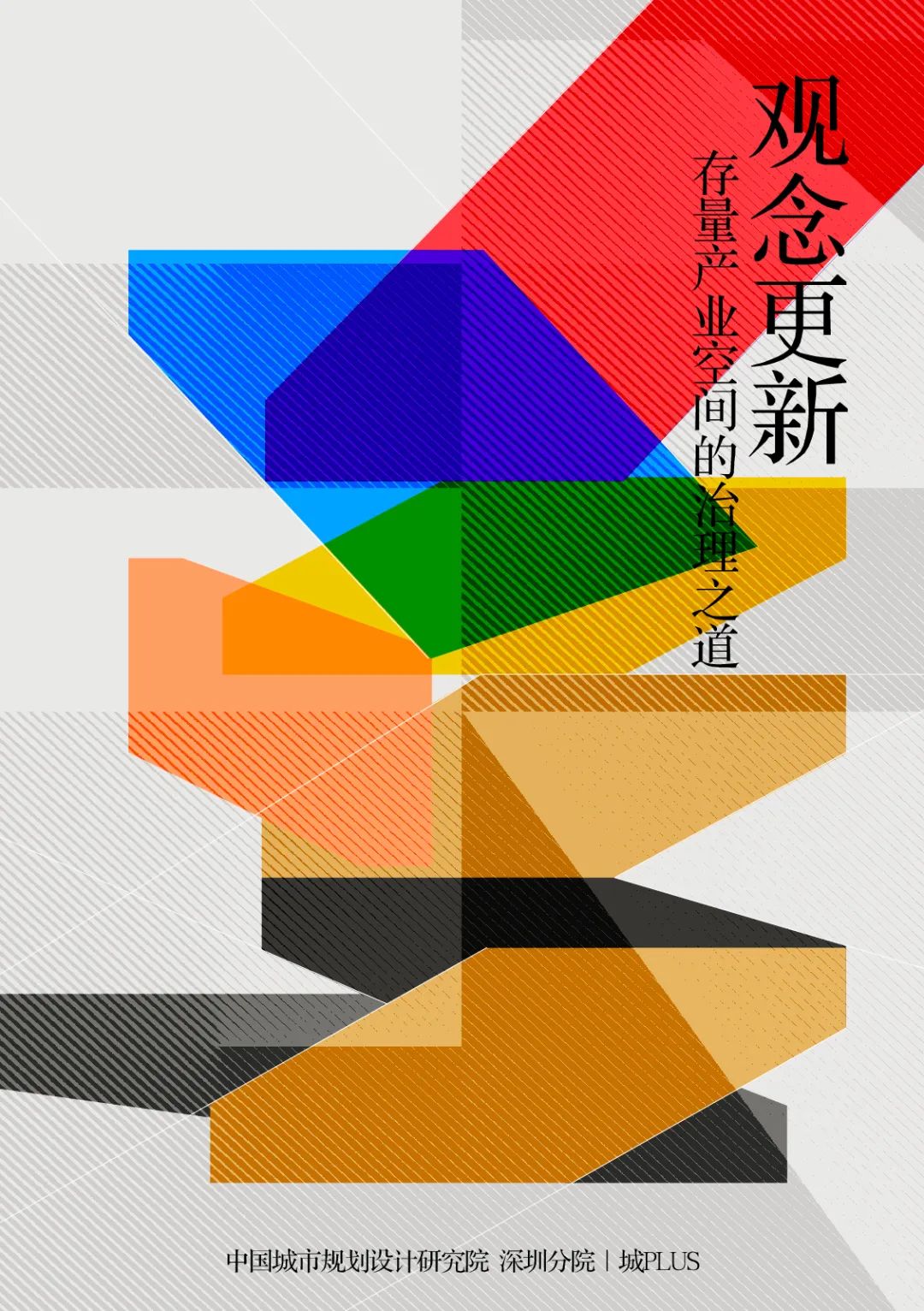
编者按:本文是中规院深圳分院存量中心在城市更新行动、深莞边界地区合作、深圳都市圈等领域展开综合实践和思考的系列文章之一,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观念更新:深莞存量产业空间的治理之道”,重点聚焦新时期、新背景下制度创新理念。下篇为“重塑边界:深莞存量产业空间的治理之法”,阐述更新整备并轨的具体算法。
从世界工厂到超级工厂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工厂”,制造业产业空间规模大。深圳现状建设用地超过970平方公里,其中工业用地约223平方公里,占比仍接近23%;东莞现状建设用地超过1240平方公里,其中工业用地约471平方公里,占比高达38%。
深莞两地拥有大量灵活应对市场变化的“轻资产”、“好掉头”的村镇工业园,是其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的空间基础。随着世界科技产业发展、大湾区科技创新突破的到来,未来将需要更多承载卡脖子技术、关键先进制造环节的“超级工厂”。
如何在一些“碎片化”的低效产业空间基础上实施“科技再工业化”,孕育更多华为、比亚迪、腾讯、vivo、OPPO等优质的企业,成为深莞两地共同的迫切追求。
现行二次开发政策反思
深圳、东莞都迈入了存量发展时代,两市都施行土地整备(土地征收)、城市更新“双轨并行”的二次开发政策。其中,城市更新强调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激活市场活力并运用市场资金,促进城市空间的更新改造;土地整备则强调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政府财政出资,收回土地使用权,解决较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及重大项目落地问题。面对新时期、新阶段的城市发展目标,现行二次开发政策的问题突出:
2.1 中心城区城市更新经验不适用于非核心地区
深圳的二次开发政策源自于“特区内”(亦即现在的城市中心地区)的项目经验总结,不论城市更新、土地整备,其空间结果都是导向“功能更加混合”。而城市中心城区因为已实现服务业化、公共交通可达性高、公共设施服务均等化,因此与政策的匹配度高。
但是适用于中心城区的存量空间开发政策扩大到全市范围,面对制造业依然重要、公共交通可达性低、公共设施严重短缺的外围地区,促进功能混合的政策表现出“不适应性”。如单一产业类城市更新项目内,允许30%的配套建筑量政策事实上非常“鸡肋”,因为既不能满足产业用地集中连片的产业需求,也难以达到高品质优质城区的服务需求。宿舍、公寓等“类居住”功能与生产制造功能难以兼容。
2.2 农用地整备经验不适于高密度城市化地区
过去的土地整备(征收)对象以农用地为主,单位用地所需整备资金小,能够实现的整备(征收)用地规模大,留用地的空间安置相对简单。进入存量二次开发时期,土地整备(征收)主要对象变成现状高密度建设的工业区,资金成本大幅提升。
在现有的土地整备机制下,整备连片的产业用地往往需要留用小规模居住功能和商业功能,导致小片区内工业和居住混杂、功能相互影响,社会效益不佳。
城市政府的土地整备金有限,所以深圳、东莞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二次开发。不同性质的资金其投入、退出的路径不同,进而会影响到二次开发的结果。我们将二次开发资金分为3类:
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制度并轨的新机制
新机制应以实现多方共赢为目标,引导不同性质资金进入各自擅长的领域,并通过“利益趋同、空间腾挪”实现城市整体空间的布局优化提升。
政府土地整备实施操作难点在于居住留用地规划安排。如果项目规模足够大,比如宝安区燕罗整街统筹项目,就容易形成功能合理分区、产城融合的空间形态。如果项目实施规模小,在本项目内留用居住用地,就可能导致空间碎片化、功能混杂,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异地安置居住留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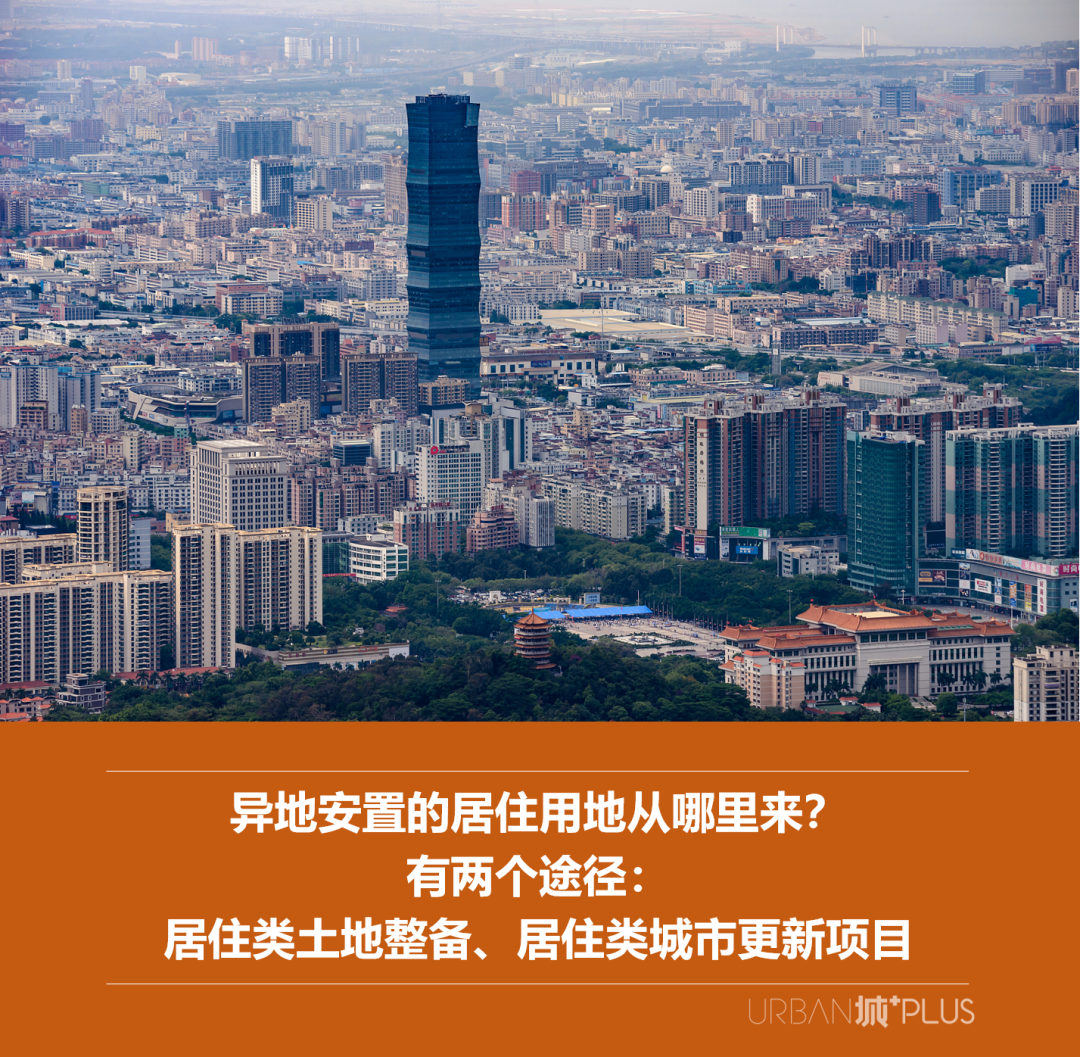
理想状态下,所有涉及功能改变为居住用途的二次开发项目应采用土地整备政策,但这将导致政府土地整备金支出压力大大增加。那么能不能在城市更新中实现收储居住用地呢?
早在一年以前,我们已提出了深莞存量开发政策创新的基本思路:“拧开水龙头,让空间资源流动起来;利用现有政策基础,精准微调”。(点击阅读:深圳存量空间的创新治理)
在存量产业空间再开发领域,我们更为具体的观点是:制定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制度并轨机制,重点关注两个基本原则: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第七条,城市更新项目由物业权利人、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以下简称市场主体)或者市、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未来工改工项目中应淡化“房地产类企业”,鼓励工业企业自改,以实现真正能适应先进制造业的建筑空间形态,避免“房地产化”的倾向。
以本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为契机,坚持规划引领,精准识别“工改居”、“工改商”项目区域,引入市场力量,推行“工改居”、“工改商”城市更新项目与土地整备项目统筹联动。允许土地整备项目留用地在“合适的功能区块异地安排”;要求功能改变类城市更新项目增加贡献经营性建设用地。
4.3 在功能改变类城市更新项目中,引入“权益容积”概念
在“利益趋同”的大原则下,建立“权益容积+增益容积”为 嘛 1更新和土地整备利益并轨机制,有助于减少因为规划功能差别带来的增益差异,稳定权利人和市场预期,重塑“规划权威”,实现一张蓝图整体统筹。
4.4 在功能改变类城市更新项目中,明确贡献经营性用地定量计算原则
允许且要求功能改变类更新项目贡献经营性用地,那么如何量化贡献规模成为焦点问题。在实操中,同一项目可先以土地整备利益算法确定政府净收益;反向要求同一项目如果采用城市更新政策路径,确保政府的净收益趋同。真正实现“利益趋同”、“制度并轨”。即:
政府通过市场资金运作的城市更新新模式获得“经营性土地+补缴地价+公益性用地”多重收益,既可缓解短期内政府土地整备金过大的压力,也可实现政府与业主双赢,极大提升二次开发项目的可行性。
结语
存量二次开发所带来的想象空间巨大,空间治理所有的创新可能都蕴含在其中。深圳、东莞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现在仍然保留着相当规模的低效工业用地,这些资源恰恰是新时期城市完成“结构性”调整并实现产业升级的机会所在,与时俱进地在机制、制度、标准层面进行调整,可以切实提升城市空间资源的调配能力,并最终保持地区持续的发展活力。
–
相关阅读
–
作者 | 杜宁
中规院深圳分院规划设计一所 主任工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硕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规划一所主任规划师,存量中心主任,近年来负责项目《深圳国际会展城综合规划》、《香蜜湖片区城市设计》等。
作者 | 周俊
中规院深圳分院规划设计一所 所长
作者简介: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长期立足深圳、深耕湾区、服务全国,擅长总体规划、概念规划、枢纽规划、城市设计。主要项目经验包括: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建设部一等奖)、惠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广东省一等奖)、深圳市大空港地区综合规划(国优二等奖)、深圳空港枢纽地区综合发展规划、深圳湾超级总部控制性详细规划(广东省二等奖)、东莞长安滨海新区概念规划(深圳市一等奖)、深圳市产业用地标准研究(广东省一等奖)等。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PLUS):观念更新:深莞存量产业空间的治理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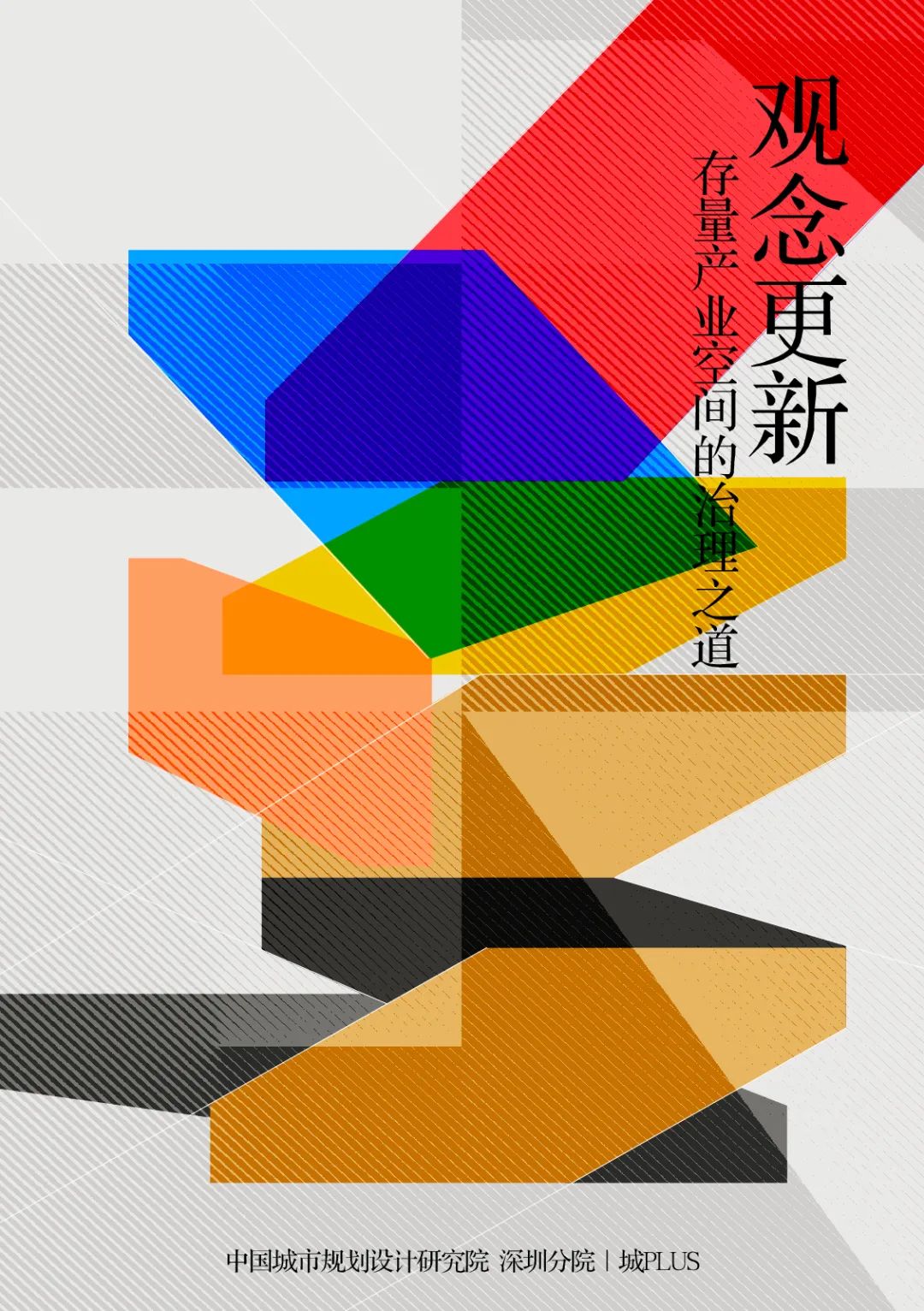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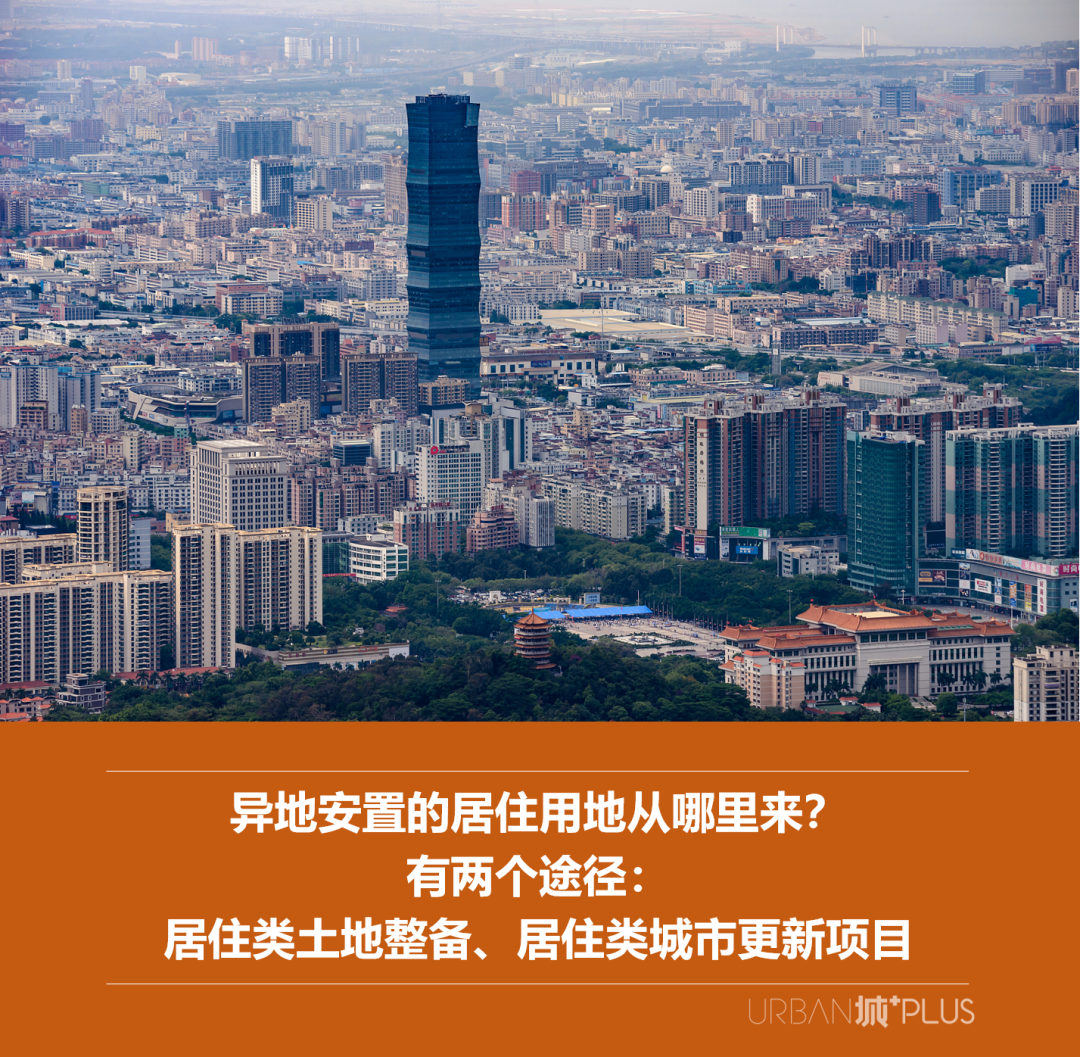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