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20年8月开始,梁鹤年先生受《中国投资》杂志邀请开设专栏,将他对中国与国际种种问题的思考写成杂文,与读者交流探讨。本号则从今年4月20日开启了新专栏——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四位青年学者将在本系列连载中分享他们阅读这些文章的感悟。
西方古典自然之法最初来自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自然秩序是法律与正义的基础,是评价和批评人为之法的依据,是制定人为之法的根据和唯一衡量标准。阿奎那进一步推演,指出自存和共存是自然之法的第一原则,人的生存和延续不能孤立于天地之间,自存与共存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制衡关系。梁鹤年先生论证提出“共存是自存的最佳保证,自存是共存的最佳标准”,从而给出了自存与共存平衡的明确的评价准则,并通过“待人如己,换位思考”的小故事,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存与共存平衡智慧。
自存、共存互相依存,互为参照,并且以适当的相互制衡方式共构和谐。共存到什么程度合适,以自存获得的最佳保证来衡量;自存到什么程度为限,以能否实现安定和谐的共存来评判。这种参照制衡关系,在《道德经》第二章中给出了想象丰富且形象的阐述:“天下皆知美则恶已存在,天下皆知善则不善也已存在。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它们的关系与“阴阳”的概念一样,看似是对立的存在,实则是极致的相反相生、相互彰显、相互制衡。
“城市人”理论的核心是自存与共存平衡,从人的“物性”“理性”“群性”三个层面来看,不同的人、事、时、空会产生不同的平衡点。辨别这些平衡点需要智慧,站稳这些平衡点需要操守[1]。因此,坚持自存与共存平衡,必须懂得择善固执,即擅用智慧辨别自然之法并坚守。
从“物性”层面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技如何发达,人的“物性”变化不大。比如:从古至今,人的步行速度一直是4km/h左右,这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古代生活性城市的半径范围,也是现代城市日常生活空间范围研究的着眼点。再如:合理的城市密度一直是城市建设关注的重点之一,而资料显示,战国时代墨子提到城市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2.2万人,1950年代初期北京老城区的人口密度是2.3万人/km²,扬州老城区当年的人口密度是2.3万人/km²[2]。这种漫长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相似的人居密度特征,必然受到了人的某种“物性”的制约。所以,我们孜孜以求的以人文本的城市空间设计,其自存—共存平衡点必然要着落在充分关照人的“物性”上面。
从“理性”的层面看,自存与共存平衡是一种智慧的辨别与选择,不同的人、事、时、空,会产生不同的自存与共存平衡点。过去我们是以经济理性来主导规划,未来可能要转向社会理性,用社会理性来校正被过度考虑的经济理性。如此,我们在关注规划的价值时,不仅要算它的经济价值,还要看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2]。
从“群性”层面看,今天人们聚居到城市是为了获取更加丰富多样的空间接触机会,以满足不断提升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在不同人、事、时、空背景下,准确把握人的“物性”和“理性”特征后,怎样才能满足人们的最优空间接触机会,就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和辨别的自存—共存平衡点。
总体而言,在特定的人、事、时、空情景下,充分关照人的“物性”“理性”“群性”,是将抽象的自存与共存平衡思维进一步方法化的途径。
[1] 梁鹤年. 自存与共存平衡[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1(Z4): 20-21.
[2] 梁鹤年, 沈迟, 杨保军, 等. 共享城市:自存?共存?[J]. 城市规划, 2019, 43(1): 25-30.
作者:于东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众人拾柴火焰高
2021年3月《中国投资(中英文)》刊载的梁鹤年先生《自存与共存平衡》一文中提到,古典自然之法中,“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是第一条法则[1],而人通过理性总结得出,美好、幸福即善的人类行为必须通过维持自存与共存的平衡才能达到,这点无关道德,也不因人、事、时、空的改变而变化。
自存是共存的基础,共存是自存的保障[2];自存是考虑共存的自存,共存是包含自存的共存。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是人类共识和常识。《中庸》所说“义者,宜也”。所谓“宜”是分寸、合适,运用到经济维度就是综合考量下的利益平衡。在集体精神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能较为充分地认识这种关系:自我发展是基础,不能损坏他人的基本利益;大家的共同进步是自我发展的保障,少不了自我发展的助力和支持。
15世纪以来,占全球20%的西方人口用500年的时间占用全球80%的自然资源进行工业革命,发展全球资本,达到了目前的物质水平。这种以消耗全球资源为基础、极端利己主义的西方文明难以为继,只有以人类生存和延续为第一普世原则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模式才有未来。与之相比,占全球20%人口的中国用中国特色可持续的经济模式,经过40多年努力达到了今天的发展局面,其间秉行的是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尊重全球的生态发展理念,即自存和与全球共存的平衡的人类文明主张。
提倡并推动国际合作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充分体现出自存与共存平衡的理念。今年10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强调“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从自存与共存角度解读,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发展、与全球发展,正如我、他和大家的关系。这不是单独的、割裂开来的个体与整体,而是整体之中的个体与整体本身的关系——整体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众人拾柴火焰高”,10年来,“一带一路”合作网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签署共建合作文件,在20多个专业领域建立了多边合作平台;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3]。这些趋好形势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自存与共存平衡理念可以作为基本原则,解决目前全球各国发展之间的异同、矛盾与纠纷,运用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普适性,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而“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内涵,与自存与共存平衡理念本质内涵高度契合;二是全球合作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个性化消费、精准化生产将取代工业革命以来的标准化生产与消费,合作型经济会胜于资本密集型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一带一路”的前景正是如此。
[1] 梁鹤年. 自存与共存平衡[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1(Z4): 20-21.
[2]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209-232.
[3] 中青在线.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EB/OL]. (2023-10-18)[2023-11-07]. 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2023-10/18/content_OVbgbNfWyK.html.
作者:王冬银,博士,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统筹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如何找到自存与共存的平衡点?
上一篇《自然之法》中,梁先生阐释了人不仅追求自我保存(自存),同时还追求与人共存(共存)。更确切地说,追求自存与共存平衡是人的理性使然,即自然之法,这适用于一切人际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自存与共存的平衡点不是“中间点”或“平均点”。正如梁先生形容的,自存、共存、自存与共存平衡三者并不是黑、白、灰,而更像是黄、蓝、青——“灰”或者灰色地带隐含着黑与白的叠加或增减调节,带有一种避免非黑即白争论的妥协感或安全感;而“青”更像是基于黄与蓝的一种创造与突破,是超越黄与蓝的全新状态。也就是说,自存与共存平衡是超越自存和共存的第三种状态。而且,平衡具有过程性,不存在一个终极的平衡点,特定人、事、时、空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平衡点。
然而,理性认知不等于行为选择。正如本篇中指出的,“选择按自然之法或反自然之法去生活就是道德性的选择”[1]。理性认知是一回事,行为选择是另一回事。尤其,追求“自存”不需要引导,正如“经济人”假设描述的那样,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被看作个体行为的基本动机;相较而言,追求“共存”就没有追求“自存”那么明确,它要么被看成利己的权宜之计,要么被看成少数人甘于奉献的崇高美德,再或者,它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受。正因为如此,找到自存与共存的平衡点并不容易。
以南京市城市更新过程中首个“自拆自建房”为例[2]。从2014年二层小楼被鉴定为危房且产权人申请自筹资金翻建,到2022年交房二十余户业主搬入新家但仍未落实产权证。从自存与共存平衡的角度来看,长达近十年的沟通协调过程有三点值得思考。
第一,特定人、事、时、空产生特定的“平衡点”。不同的人(如不同住户和相关政府部门等主体)、事(如居民意见整合、设计方案协商等事项)、时(如申请立项、方案审查、施工建设、产权证办理等不同环节)、空(如支持性的政策环境等)会呈现不同的“平衡点”。
第二,存在该楼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内部平衡”和该楼与其他楼栋改建项目之间的“外部平衡”两个层面的平衡。“内部平衡”主要指该楼的改建设计方案如何平衡各业主的自存诉求与小楼整体改建的共存诉求;“外部平衡”主要是该楼的改造验收标准如何平衡该楼改造的可行性诉求(自存)与政府规范老旧小区改造行为的建筑标准及要求(共存)。本案例的实践过程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南京市城市更新中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改革实施方案(2.0版)》,它针对“三原”项目(原址、原面积、原高度改建)作出了明确规定。
第三,自存与共存平衡的理性需要制度引导。该案例是南京市“自拆自建”模式的先行先试,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是张玉延作为居民代表近十年的东奔西走与热心奉献。然而,在此过程中,不仅出现政策空白导致的申请批复困难重重的情况,还出现居民利益分化导致的不同主体之间的长期拉锯,甚至出现了“倒张派”与“挺张派”的对峙。正如报道中评论的,“关键在于人和制度保证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制度保障,那就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最终很难成功”[2]。也就是说,自存与共存平衡虽然是人所共有的理性,也因此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公民意识提供了基础,然而,要在平等协商过程中推动特定群体选择自存与共存的平衡而不是仅考虑自身利益,既需要在社会道德层面倡导“大我”精神,也离不开制度层面的规范与引导,后者提供了可行的操作路径和坚实的权益保障。UPI
[1] 梁鹤年. 自存与共存平衡[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1(Z4): 20-21.
[2] 新京报. 首个“自拆自建房”,困在“最后一米”[EB/OL]. (2023-10-09)[2023-11-01]. https://news.sina.com.cn/s/2023-10-09/doc-imzqnhxq9542916.shtml.
作者:李媛,博士,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治理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系列文章
01 解读《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梁言实录 | 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连载】(10)解读《自存与共存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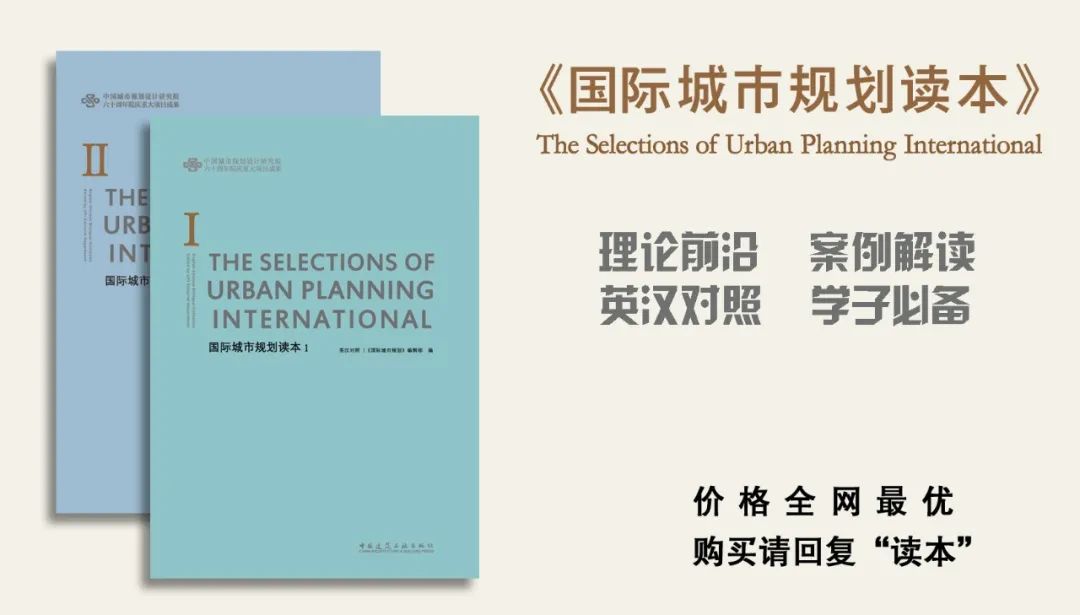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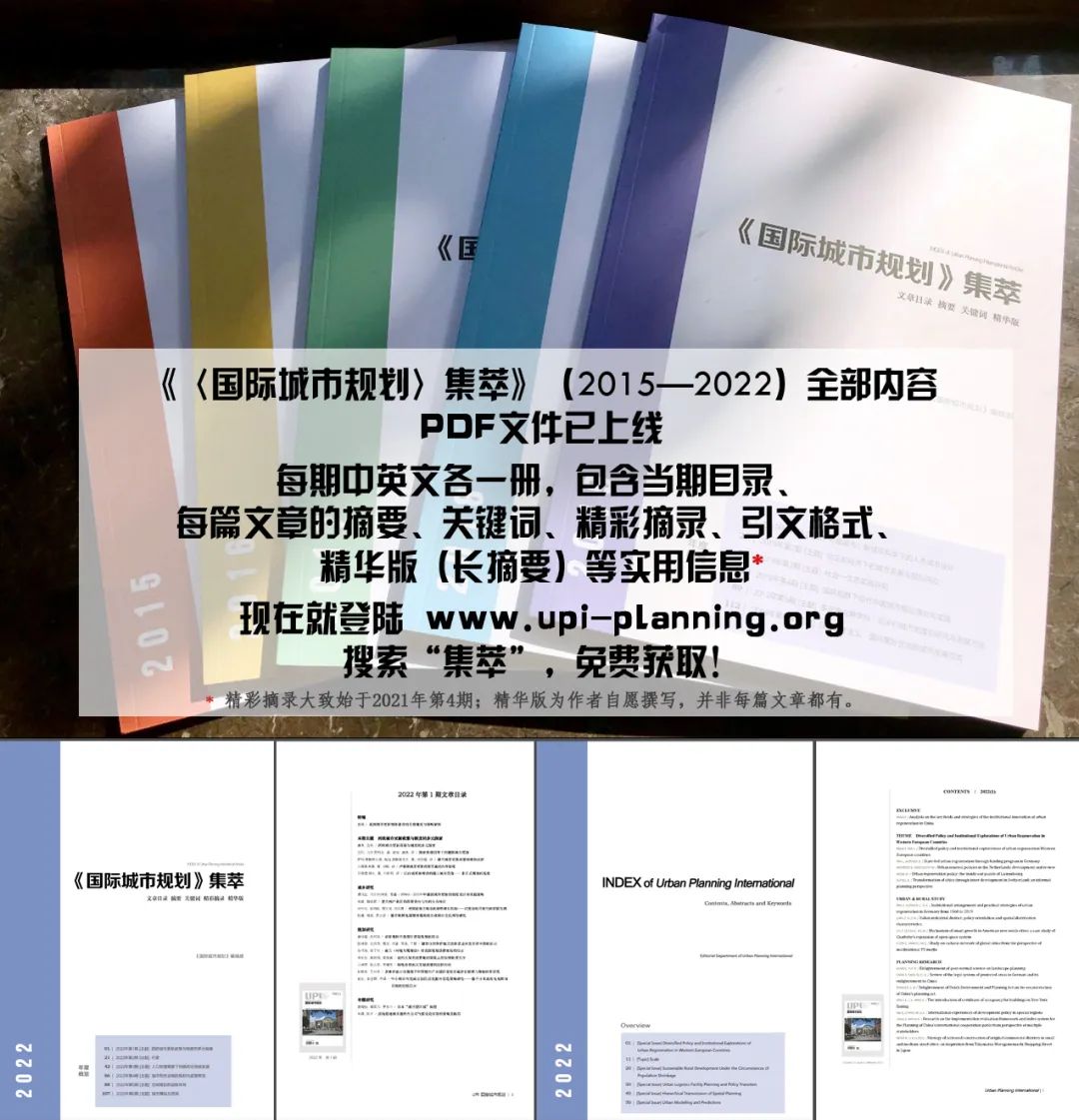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