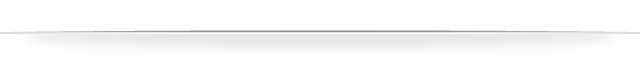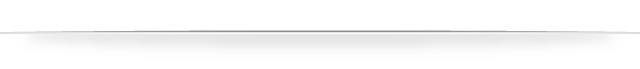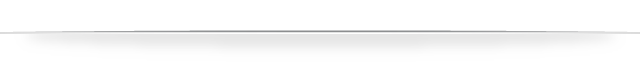历史钩沉—-首都规划及规划管理工作实践方面的历史回忆纪实。
建国以来首都的规划工作,道路漫长,历尽艰辛,其中曲折复杂、千变万化的协调、决策过程鲜为人知。在这里我们请老一辈规划工作者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把精彩纷呈的历史事实写下来,作为正史的补充和解读,以帮助后人进一步深人理解首都的规划建设实践。
本文选自“首都城市规划事业60年纪事”征文。谨以此篇向郑天翔前辈表示崇高的敬意。
郑天翔,原最高人民法院第七任院长,原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主任
关于造林绿化问题
在绿化方面,我们采取了特别强调植树造林的方针,诚如一些人所说是“大绿地主义”。1953年规划要点即提出“必须增设公园,大大扩大市区内外的绿地面积”,“在北京西北和北面的山区普遍建造大森林,在市区境界外围建立巨大的防护林带和防护林网,以防止风沙袭击,并作为污浊空气的过滤所和新鲜空气的储藏所”。
关于北京市区及山区的绿化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都很关心,多次给予指示。彭真同志多次向市委领导同志和做规划的同志传达毛主席关于要十分重视植树造林的谈话。毛主席始终关心北京的绿化。1959年9月,毛主席视察密云水库时,指着周围的山头问:把这些山头绿化起来,用得了一百年么?我和在场的同志们都回答,用不了一百年。回来以后,我们向刘仁和市委其他领导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话,决定把水库周围绿化继续抓紧。
北京市委市政府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指示,一直把造林绿化放在重要地位。1955年以来,市委几次发布植树造林的决定,并组织实施。在进行总体规划期间,彭真同志多次提出,越是人口集中的地带,越要重视植树。
“总体规划”提出:北京的北面、西面,群山环绕,城内外又有不少名胜古迹,这些是绿化首都的优越条件。把西山,北山全部绿化,使它变成首都的绿色长城,防御风沙,改善气候,养蓄水源。这个规划,从绿化小西山开始,于1958年大规模组织实施。那时,中央党政军机关以及市属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组织力量上山,安营扎寨,分片包干,植树造林。八达岭一带的长城内外和昌平部分山区的苍松翠柏,有许多是四十多个中央机关从1958年开始种植的。城内的积水潭、什刹海、北海、陶然亭、天坛、龙潭湖等和城外的颐和园、动物园、玉渊潭、圆明园、水碓湖等等都是全市性大公园。我们考虑到朝阳区工业集中、公园很少的情况,特别强调了水碓湖公园的建设;根据当时的状况,规划面积四百三十多公顷,大约为中山公园的二十倍。
“规划”提出:还要在居住区内,普遍开辟小公园;在工业区和住宅区之间,建造宽度不同的防护林带;在机关、工厂、学校、医院院、住宅内部和周围,在路旁、河旁、渠旁以及铁路两旁、高压线走廊、水库周围等一切可以绿化的地方,都要绿化起来。这些林带、林网、公园和大大小小的绿地,组成了首都强大的绿化系统。
“规划”提出:绿化是城市中的一项巨大生产事业。植树工作应该在美化城市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下,合理地安排。山区绿化应当以建造大森林为主,城市内以至公园内的绿化,也以植树为主。植树要将快长树与慢长树相结合。
关于城市的交通问题
首先是完善开阔的道路系统,其次是地上地下相结合。地下铁道初步规划为六条直线,一条环线,总长约一百七十千米。为解决首都的城市交通问题,这次规划从总体上进行研究,大体上采取了类似治水防洪的方针:
“ 减流 ”
尽最大可能减少城市客流量。主要是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性的优越性,对工业区、教学区等和住宅区,对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以及中小学校,尽可能按就近上班、就近上学的原则合理安排,尽可能避免长距离上班和上学。对公共建筑合理均衡分布,多方开辟公共活动场所,大力避免参观游览流向流量过分集中于少数点线。
“ 截流 ”
主要是加强新建区域、新建大单位和卫星城镇的商品供应、生活服务、文化娱乐设施并提高其水平,尽力避免大量客流向城市中心集中。
“ 分流 ”
除了保持前门、王府井(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商业服务业、文化娱乐场所综合在一起的全市性繁华点以外,在建国门、复兴门、朝阳门、阜成门、安定门以外及海淀一带,新建若干个繁华点,加强其综合性,提高其服务供应水平,同时,把某些地方(如大栅栏一带)过分拥挤的商业等单位转移一部分,尽可能把汇集于少数点的人流分散开。城市发展的方针,不是将已经集中的客流进一步引向中心区,而是将集中于中心区的客流尽量可能分散出去。
“ 限流 ”
采取严格的长期不解的措施限制首都人口的增加,同时,大力限制首都过量的流动人口。
“规划”对铁路枢纽做了重新布置,主要是增强其畅通性,减少穿过市中心区的线路。
道路交通问题,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要素。交通阻塞是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是生产力的浪费。马克思说:“一切的节约,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这个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采取统筹全局,增强计划性,避免盲目性,增强综合治理,避免畸形突出,才可能有效地解决。总体规划只是提出基本的方针,具体问题很多,需要在具体规划中具体解决。
关于首都建设的艺术形式问题
1953年规划要点提出:“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在城市的布局及其艺术形式各方面都能反映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日益高涨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超越以往历史时代已达到的成就,并且为后代的发展尽可能留下充分的条件”。1958年6月,市委就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向中央作的报告中提出:永久性的建筑“应该适当讲究艺术形式,把适用、经济和美观结合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面貌,首都的建筑艺术形式,既不能沿袭、束缚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旧都市和建筑的风格、结构和框框,也不能雷同于那些资本主义大国的首都或西方大城市的面貌,而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1955年,建筑界批评过建筑上的复古主义,批评的对象是:对于旧有的建筑,不论其价值大小、是否直接妨碍城市的发展而一概保存、一概不能动的主张;不论什么建筑都要采取“大屋顶”的艺术形式。当时和在这以后,市委没有否定中华民族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及技术方面的优秀传统。在建筑史中,中华民族有其独立的、卓越的成就,独树一帜,称雄于世,影响广远。中国建筑的优秀成果是民族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忘掉自己的祖先,对一部中华民族建筑史,对无数吸引世人景仰的古代建筑的卓越成就,采取否定一切的狂妄态度,对外国时髦的建筑风格,顶礼膜拜,唯恐抄得不快,抄得不像,抄得不全,这是很有害的。
关于首都建设的经济问题
这里说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指城市建设中市政投资的节约和土地的节约。建国初期,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用房的迫切需要急待满足,又由于要考虑战争,而且当时不可能迅速提出一个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新建筑的布局是比较分散的。这样分散下去,势必要增加电力、道路、通讯、上下水、物资供应、商业服务、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投资。在进行总体规划时,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把城区规划范围扩大到六百平方千米左右,同时强调了首都的发展既不应把六百平方千米建成一个大块,也不宜在六百平方千米范围内任意设点,而是采取了城区外围集团式发展的方式。
集团式发展就是把新建筑较多的地块划定范围,加以充实、完善,因势制宜,使之各具特点,自成章法、同中心区既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尽力避免到处铺摊,零星布点。因为,每铺一个摊,每布一个点,就会带来一大堆问题,不花钱是难以解决的。
集团式发展意味着节省土地、保持大块的菜地农田。北京的建设不可避免要占用相当多的农田,但是要力求节约、要力求避免把大块农田切成碎块。否则,就等于多占了农田,妨碍农业的现代化。大块农田、大片树林与集团式发展起来的工业区、文教区、居民点(包括农民居住区)有计划的结合起来,就增加了城市的绿化面积、形成城乡结合、缩小城乡差别的局面。
为了避免市区臃肿不堪,就需要发展卫星镇,尽力分散大批建设单位到卫星镇。卫星镇的建设也需要攥成拳头,形成独立完整的布局;也要尽力避免处处开花,零星布点。在郊区,建设在卫星镇以外的单位,也要采取集团发展方式,极力避免任意零星扩散。
首都市区规模最大控制在六百平方千米。市区城市人口(不包括卫星镇人口),最高控制在六百万。人口太多了,市区太大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很不经济。因此,控制人口并限制一些单位设在北京,始终是一个严重的任务。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发展与限制同时并举,在发展的同时就极力限制其规模。我们们采取这样一个战略布局、战略方针,力求使首都保持健康的风貌、良好的环境,避免陷入外国一些大城市盲目发展、不可收拾的困境。执行这样的方针,难度很大;放弃这样的方针,其害无穷。这是一个难题,需要在总体上和具体建设上不断地研究、解决。
关于城区改建问题
1958年6月,市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虽然解放以来我们盖的新房已经有二千一百万平方米,而城内古老破旧的面貌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根据中央和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准备从1958年起,有计划地改变这种状况。北京城内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平房,而且多数年代已久,质量较差,还有相当数量已成危险建筑,每年都要倒塌成百间以至上千间,比起上海和天津,改建起来,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从改善城市交通的需要来看,也必须对城区进行改建。我们初步考虑,如果每年拆一百万平方米旧房,新建二百万平方米新房,十年左右可以完成城区的改建。”
当时估计,除故宫等古建筑外,城区有旧房一千六百万平方米。其中,大约有百分之七十左右需要改建;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旧建筑,包括那些质量较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合院平房可以保留。
1949年到1957年底,城内每年平均新建房屋五十多万平方米,其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新建房屋七十多万平方米。那时,宣武区西半部有大片空地可以新建;往后的新建,主要靠拆除旧房。由于平房院内人口和小房子逐年猛增,因而每年拆除大约一百万平方米旧建筑,这使新建约二百万平方米房屋的计划不好安排。我们在1958年设想的“十年左右基本上完成改建城内破旧平房”的打算难于实现了。后来,平房院内人口愈来愈多,改造的难度愈来愈大,到“文革”爆发,城区改建进展不大。
1958年6月,市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改建城区,首先要从中心区开始,要采取成街成片逐步改建的方针。拆一片就按照新的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建一片,建成新的街道和居住区。”
按照统一的规划和设计进行改建,改建一街,建成新街;改建一片,建成新区。对这个改建城区的方针,市委在这个报告之前和以后,曾多次强调。同时,市委多次提出,对于市政设施要坚持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先地下、后地上统一实施的原则。市委也多次提出,在改建中力求避免无统一规划、无统一设计、无统一筹划,满城开花,孤立改造,新建不少,面目依旧的局面;力求避免有了房没有供水,不能排水,没有路,没有电,没有电话的局面。
总结我们的教训,主要是在进行总体规划时,只注意了总体平面布局,没有同时研究城区的立体总体布局;只做了总体规划,没有同时做分区规划。北京城的平面是一个统一布局的协调整体,立面也应当是一个统一布局的协调的整体。没有立面的总体规划,没有在进行总体规划的同时抓紧进行分区规划,致使改建城区缺乏完整的规划依据或分区规划脱离总体规划。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关于对执行总体规划的干扰问题
“文革”前,在首都建设中,干扰“规划”执行的,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数量越来越多的违章建筑;第二,是名为“临时”实则“永久”的临时建筑。这里,主要讲一下“临时建筑”。
在首都的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有一些临时建筑、临时设施。因为它是“临时”,往往没有周密考虑而“临时”处置。结果,往往陷于被动。
如中山公园内的音乐堂,最初只有露天设施,为的是临时使用,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一个几千人集会的地方。随后,因为要挡风,建了围墙;随后又因为既然有了围墙,为了遮雨,加加了盖子,于是形成了一个与周围景物很不协调的庞然大物。又如,故宫东西墙外筒子河边的两大片建筑,当初是临时工棚。临时工棚在施工任务完成后,按理是要拆除的,可后来有相当一批工棚演变成为正式的建筑。也有的建筑,1953年修建时就说好是临时设置以应急需的,什么时候叫拆就什么时候拆。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住宅院内搞起了一些违章建筑,也说是“临时”,可拆迁起来还要作为要价的筹码。如此种种,在规划管理面前就摆着一个难题,不搞“临时”建筑不行,搞了“临时”建筑,有许多就不是“临时”,就会冲击整个规划方案。
有些“临时”,是因为总体规划或规划管理考虑不周造成的。例如,总体规划中,对公共交通的停车场、车站等方面用地,打得不足。又如,许多理应留下足够停车场的建筑,为求一时之省,不留停车场或停车场留的很小,结果汽车在楼前面乱作一片,甚至沿着马路摆,占了人行道,挤了交通线,造成了混乱、难堪的局面。再如,对于必须拿出停放大量自行车的场地,在总体规划时没有预计够,在规划管理中缺乏相应的处置,结果,自行车摆满某些街巷、摆满许多庭院,甚至上了楼。
“临时”影响长远,局部干扰全局,反映了首都建设中暂时和长远、局部和全局的矛盾。我们在当时考虑不周,处置无力,给总体规划的实施造成不小的困难。
关于首都建设的管理体制问题
1958年6月,市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几年来的经验,要做到多快好省地进行城市建设,必须实行六统(即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统一管理),而六统的关键在于统一投资。1958年开始对一部分住宅实行统一投资建设,已经显示出很多好处,今后需要扩大统一投资建设的范围,即除了国防建设、工业建筑及其他特殊性的建筑以外,所有住宅、办公用房、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中小学校、商业服务业设施等,都可以采取投资统一交市,由市根据各方面的需要,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和建设的办法”。关于首都建设必须实行六统或五统,其核心是统一投资的意见。在此之前,市委也曾向中央报告过,刘仁同志在党的八大大会发言也强调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建设的统一领导,尽可能克服各自为政、互相扯皮的现象;建议在北京市的建设逐步形成总甲、乙、丙方。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对城市建设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
建国以来到十年内乱,国家对首都建设的投资一直是按条条分的。本来可以统一建设的东西,都按条条分面积、分投资、分材料,结果城市规划部门只能按条条的要求拨地,设计部门只能按条条的任务设计,施工部门只能按条条的布点来布阵。首都建设中出现的许多弊病,首都总体规划实施中遇到的许多困难,城市建设中本来可以节约的投资和土地不能节约,旧城面貌长期不能从根本上改观,都跟这个计划和投资体制有关。经验证明,集中统一地进行建设,就可以多快好省;反之,效果就差。“文革”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统一投资,其他方面的几统是办不到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是应当也是能够解决的。
以上,我根据1957年制订、1958年上报中央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和市委的有关文件,对”文革”前首都的规划和建设问题做了记述,首都建设的总体规划,是在中央、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关怀和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原都委会(日常工作开始是由薛子正同志主持)工作的基础上制订的。从1953年到1958年6月、7月,我在市委领导下,直接主持规划方案的制订并参与规划管理工作。首都的规划和建设,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涉及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对城市建设更缺乏经验。因而在这项工作中有不少缺点、错误。前边提到的一些教训和缺陷,以及工业布局上的毛病,如市区内项目摆得多了,有的地区摆得挤了等等,和我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分不开的。
在首都的规划工作中,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城市规划和规划管理专家。他们对首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梁思成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建筑专家,学识渊博,对工作认真负责,长期担任都委会和规划委员会的副主任,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见解。北京设计院著名的工程师朱兆雪、杨宽麟,著名的建筑师张镈、杨锡镠、张开济、赵冬日、陈占祥、华揽洪等许多同志,以及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部分师生,国家建委设计院的一些专家,在首都的规划和建设上,都作了重要的贡献。梁思成、朱兆雪、杨宽麟、杨锡镠同志已逝世多年,在此,谨表示怀念之情。
 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京津冀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