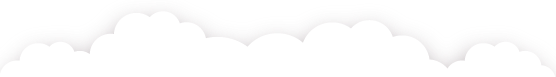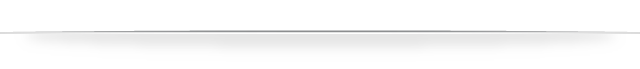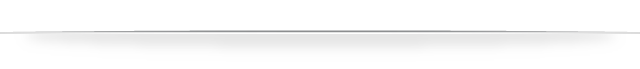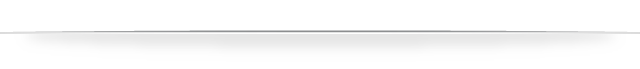历史钩沉—-首都规划及规划管理工作实践方面的历史回忆纪实。
建国以来首都的规划工作,道路漫长,历尽艰辛,其中曲折复杂、千变万化的协调、决策过程鲜为人知。在这里我们请老一辈规划工作者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把精彩纷呈的历史事实写下来,作为正史的补充和解读,以帮助后人进一步深人理解首都的规划建设实践。
本文选自“首都城市规划事业60年纪事”征文。谨以此篇向郑天翔前辈表示崇高的敬意。
郑天翔,原最高人民法院第七任院长,原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主任
1949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市长兼任主任委员。叶剑英同志南下后,聂荣臻市长兼任主任委员。抗美援朝开始后,聂荣臻同志集中精力于总参工作,彭真同志兼任市长,兼任都委会主任。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心首都建设的总体规划。市委、市府也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总体规划主要是解决首都建设中带有全局性质的问题即战略部署。
1949年9月,中央请来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首的十七人的苏联市政专家团。经过短期考察,专家团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建议,示意性地规划了北京城近郊土地使用方向,提出了行政中心区、工业区、文教区的布署方案。聂荣臻同志亲自主持市政府会议,讨论这个建议。这期间,有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即是不是要放弃旧城在西郊另建“新北京”的问题。根据北京城的实际情况(有相当数量的房子和市政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可以用)和当时的具体情况(已经有中央和军委的许多领导机关进驻城区)及国家的财政情况(当时和以后相当时期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另建一个新北京)。中央和市委市府同意专家团的建议,确定了以北京城为中心逐步扩建首都的方针。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北京的建设任务大大增加。都委会忙于划拨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的管理,不可能腾出手来研究比较具体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市委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组成了一个精干的班子专门进行总体规划方案的研制。规划小组在都委会初步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市委于1953年11月26日上报中央。1954年又作了局部修改,并制定了“北京市第一期1954年-1957年城市建设计划要点”,市委于1954年10月24日上报中央。1953年的规划要点提出首都建设的总方针,并对一些主要问题提出明确的意见。但是,当时我们对许多与制订规划草案有关的情况来不及做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各方意见不一,争论很多,有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1955年2月,市政府成立了都市规划委员会,从各条战线调集了一大批专业人才,组成包括城市建设各方人员的工作班子。同年4月,苏联城市建设九人专家组到京,随后,又请来了苏联地下铁道专家组,进一步研究和编制首都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工作,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全面展开。规划委员会的干部差不多都是刘仁同志亲自从各方面精选的。彭真同志对进行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一些重大问题,多次提示,多次主持市委常委会进行讨论。刘仁同志经常深入规划工作的现场,就一些重要问题跟同志们反复研究。市委其他领导同志和各方面负责同志对规划工作非常关心,多次听汇报、看模型、提出意见。中央一直关怀首都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毛主席多次听了彭真同志就规划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汇报,并就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作了具体指示。1956年6月3日,周恩来同志在当时担任城市建设部部长的万里同志陪同下,亲临规划委员会,听了汇报,看了图纸和模型,就一些重大的争论难决的问题作了指示。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在1956年9月间,先后参观了总体规划方案的展览,给予指示。对于地铁规划方案,粟裕、杨成武、张爱萍等几位总长和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肖克同志等参观了展览,仔细听了汇报,并且给予了指示。这次总体规划工作历时两年半。初步方案于1957年春天基本定稿。市委于1957年3月进行了讨论。1958年4月,规划委员会又根据一年的经验作了若干局部修改和补充。市委又多次讨论,于6月正式上报中央;同时,以内部文件形式下发;地铁规划方案则专门向中央、国务院作了报告。
首都城市建设的总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从城市建设各方面促进和保证首都劳动人民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用最大努力为工厂、机关、学校和居民提供生产、工作、学习、生活、休息的良好条件,以逐步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次总体规划方案的制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具体地贯彻了这个总方针。我们从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从北京的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把长远的发展战略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保留历史名城的特色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就首都建设有关方面的大政方针提出明确的意见,对争论较多或考虑还不成熟的问题暂不决定,在一些重要方面留有余地,尽力避免由于我们知识和经验不足而束缚后人的手脚。在规划过程中,我们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听取不同意见,不断地进行修改和补充。
规划委员会对北京的现状,包括人口、城市用地、绿化、动力、道路、河湖水系、供水排水、道路桥梁、交通流量、公共服务设施、学校、工业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尽可能搜集了古建筑和地下建筑的资料。规划委员会和市计委联合对北京工业现状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直接间接参加调查者,有六、七千人。为了调查公共交通流量及其分布特点,连续多次动员上万人,包括许多中小学生参加;另外还对北京地区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进行大规模的勘探。为了解决北京的水源和建设水库,规划划委员会勘察和研究了黄河、滦河引水的可能性,进一步勘察了京西、京北山区的水资源和主要水库库址。关于北京的地震问题,在1954年,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负责,组成了一个包括著名专家参加的小组,详细研究了北京及其附近的地震历史资料,追查了地震遗迹,作了震级估计(“文革”前,北京建设的地震设防问题,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的)。1956年初,规划委员会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草案;1956年8月,请了市人大代表、市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市属各部门、建筑设计部门的同志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共约二千三百多人参观、征求意见。在党的八大期间,从1958年9月12日至10月29日,再一次举办规划草案展览,除刘少奇等十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外,还请了八大代表、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机关干部,我国许多著名的建筑师、部分高等院校的教师、十六个省市城市建设部门以及市区县各部门的同志共约四千五百多人,参观展览,提出他们的意见;还有参加八大的三十五个国家、一百二十八位外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参观了展览。有的同志给我们介绍了国外城市建设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1958年6月,市委正式上报中央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的。这个规划方案一直规范着北京的各项建设,直到十年内乱爆发后的1967年1月被勒令“暂停执行”。
1957年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和市委的有关文件,对首都建设的主要问题以及同执行规划有关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如下的方针和意见:
关于首都的性质和发展规模
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和经济中心。首都的经济支柱是高质量、高技术、多品种的现代化工业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农业。
北京旧城为六十二平方千米,市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六百平方千米。东到定福庄,西至永定河,南到大红门,北至清河镇,在六百平方千米的规划市区采取集团式发展方式,即这个区域不联成一片,而是中间保留几块大片菜地和农田,建设林带和森林公园,从当时已经形成的分布局面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制宜地形成若干密切联系而又相对隔离的各有特征的建设区。这样可以使市区有一个较好的生态环境,城市的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供应比较方便;同时,也考虑到备战问题。在市区周围建设卫星城镇,采取“子母城”的发展方式。北京的城市人口严格控制,远景人口,在六百平方千米规划市区内(不含卫星城镇),将人口控制在五百万到六百万以内。
对古建筑和文物古迹的方针
对以故宫为主体的一系列古建筑,包括景山、三海,天、地、日、月四坛,顾和园以至十三陵、长城等等,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对故宫严格保持其完整性,禁止拆除改建。对天坛、北海、景山、顾和园等公园,保持原有面积,禁止侵占;有的,如北海,保留扩展余地。对广济寺、雍和宫、清真寺、白云观等,采取保护方针。对一部分反映中国庭院规划和建筑艺术的重要王府、四合院,也采取保护方针。
这个坚决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方针,具体地反映在总图上面。这同国务院在此前后发布的保护文物的命令是完全一致的。圆明园集中地反映了清王朝昌盛时期的奢侈淫逸;同时,也集中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园林规划和建筑、雕塑等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它聚集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也记录了列强掠夺蹂躏我们民族的耻辱。规划方案要求对原址全部保留,设想在国家财政可能时,重新建设为一个大公园;在进行规划的当时就采取保护措施,决定进行绿化,使之首先成为一个大森林公园。现在圆明园遗址绿树成荫,这大多是50年代发动群众和园林工人营造的。
对少数古建筑的拆除问题
北京城(主要是内城)继承、发扬并集中了元代以后我国封建盛世时城市规划、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等各方面民族文化的精华。皇宫是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以皇宫为中心向外展开,北起景山,南到正阳门,中以天安门为主,左右以三座门为界,构成一个扩大了的完整的建筑体系;再以城墙和各有特色的九个城门楼拱卫四周,构成了庄严的京都的总体系。在这个总体系中,包括了功能不同、高低不等、大小不一、艺术形式各异而又互相协调的建筑群和河湖园林。北京城是一个保存得最完整的出色的大艺术品,是中国古代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工匠和工人在统一的规划下集体创造的建筑成果,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自元末以来,她虽然经历了毁坏、重建、扩建和部分的改建,但始终保持了统一、完整、协调的风格,为了保护这座文化古城,保护中华民族这一份文化精华不受损坏,1949年1月16日,中央军委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出指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没有攻城,北平解放采取了和平方式。
在这样一个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封建王朝首都的基础上,进行总体规划,把它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现代化首都,必须清醒地估计和预见到它的规模、局面、古老的风格等,能否适应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首都发展的需要,必须从总体上保持和发展北京城的艺术风格,同时必须坚决进行必要的改造,对显然不能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和阻碍交通畅通的建筑物,要适当加以拆除。我们的方针是继承、改造和发展相结合。1953年规划要点即提出“既要保留和发展它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又要打破旧的格局所给予我们的限制和束缚”。警如,三座门和三座门南侧的红墙,不能适应政治活动和现代化交通的需要,拆除了;几座牌楼不适应城市交通,而且其周围建筑的风格在解放前就已经不协调了,失去了当初和谐的原貌,也予以拆除。对不甚重要、也不碍事、可拆可不拆的,如中华门等,暂时保留。有的古建筑和牌楼,拆除后移建于陶然亭公园等处。
城墙和城门楼是北京城最明显的标志,要不要拆除或怎样拆除,争论很大,问题也很复杂。1953年,为了交通方便,曾考虑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箭楼。随后的实践表明,为了疏导集中的交通流量,在交通要道道口还需要设置大小不等的转盘,证明环绕城楼可以建造成交通干道的转盘,采取适当措施,城门楼不会妨碍交通。因此,我们在规划总图上对城门楼明确予以保留。城墙封闭了城内外的联系,决定拆除;但对于是全部拆除,还是保留四周的城角,或者是拆到底改建为环城路,还是拆到一定高度改建为立体交叉的高速干道等等问题,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因而,1958年虽有过拆城墙的指示,研究结果还是暂缓行动。崇文、宣武城门楼是在修地铁时拆除的。朝阳门城楼有坍塌危险,当时又无力修缮,1956年拆下来,材料一律保存。十年内乱中,在拆除城墙时,除正阳门、前门箭楼、德胜门外,其余各城门楼通通被拆除。古城风姿,为之减色。
关于道路体系的布局
从北京城的具体情况和往后发展的需要出发,首都的道路系统宜采取棋盘式、放射线、环路三结合的方式。我们考虑到旧城原有的格局和中央领导机关主要在天安门附近,特别强化了以天安门为中心的东西、南北中轴线。东西长安街笔直地向外延伸的东西中轴线,西到石景山,东达通县,全长四十千米;以前门箭楼为起点的南北中轴线,笔直地延伸到南苑,长达十余千米;加上从景山北门起中经钟鼓楼往北延伸的南北中轴线北段,总长约二十六千米,把东单东四大街,西单西四大街向南向北打通,形成旧城内主要的南北干道;沿着东四十条经平安里到官园一线,开辟第二条横贯市区东西的大道;把菜市口、新街口、北新桥、蒜市口打通、展宽,在旧城内形成第一环线,沿城墙一线形成第二环线。主要的放射线从原有的城门口出发,城内城外联为一体。这样,就把原来以皇宫为中心的封闭的小天地改造成为一个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特色的现代化的开阔的大天地。它不是旧城的简单放大,而是体现了既对古代文化精华加以继承又根据现代化需要积极改造发展的态度。
北京道路的宽度诚如有些人所说是大马路主义。道路大体分四级:最主要干道,主要干道,次要干道和支路。最主要干道东西中轴线,东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定为一百一十米到一百二十米;天安门广场入口处,为一百八十米,南北中轴线定为九十米。东单、东四、西单、西四、东四十条贯通线和内环路等主要干线,定为六十到九十米,次要干道定为四十到五十米,支路宽为三十到四十米。王府井大街人流量大,定为七十米。居住小区内道路,宽为十米到十五米。十年内乱前的建设一直是照此办理的。不如此,整个城市交通难以畅通,而且不可能建立隔离林带,不可能建成林荫大道和在居住区大量植树。
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划
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心脏。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布局等,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为许多人很关心的问题。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阅兵,已经明确了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政治活动中心。在这里,除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这样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建筑以外,任何机关和团体的建筑设施,都不宜建。关于天安广场的规模和布局,曾经先后做过几十个方案,征求过多方的意见,最后是经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彭真同志亲自指点明确下来的,随后就按确定下来的方案建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按毛主席指点规划的天安门广场,规模宏伟,布局简洁,庄严朴素。广场东西宽五百米,天安门到正阳门,长八百六十米,面积四十多公顷。
关于水的问题
水是城市的命脉。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1953年规划要点即提出“北京缺乏必要的水源,气候干燥,有时又多风沙。在改建与扩建首都时,应采取各种措施,有步骤地改变这种自然条件”,并提出“除地下水外,必须充分利用官厅水库的蓄水,在三家店、陈各庄一带修建蓄水工程,引永定河水入城;在潮白河上游适当地点修建水库,引潮白河水入城。”1949年11月,中央就决定修建官厅水库,1951年动工,1954年5月竣工。1954年制定引永定河水进城的方案,1956年1月动工,1957年4月,把永定河水引进城来。1953年以来,规划小组和规划委员会陆续勘察了潮河、白河、滦河等水系;制订了兴建密云水库、把潮白河水引进城来的方案,勘定了引水线路,1958年6月,北京市、河北省、水力部联合向国务院正式提出修建密云水库的报告,随即筹备开工。规划委员会还曾经过勘察,于1956年4月提出在张百湾修建高坝,将滦河水引入密云水库的方案,因牵涉问题较多,未定。为了彻底解决北京的水源,我们组织工作组,考察和研究了在内蒙托克托县筑坝,将黄河水引引入桑干河、注入官厅水库的线路,并且得到山西、内蒙领导同志的赞同。这个引黄入京方案,曾经向刘少奇同志汇报过。后来,因所过干旱地区辽阔,黄河水源不足,没有定案,将这一方案报告中央请转水电部通盘研究。
“规划”提出:对引来的水必须采取统盘规划、综合利用、反复利用、保证重点、兼顾城乡的方针,充分地合理地加以利用。“规划”特别强调加强山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涵养水源。“规划”要求扩大市区的湖泊水面,在平原地区利用每一条河道,每一个湖泊、洼地、窑坑等,大力蓄水。“规划”中提出京津通航、接通大运河的设想。这取决于国家南水北调、恢复南北大运河的方案能否实现。
(未完待续)
 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京津冀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