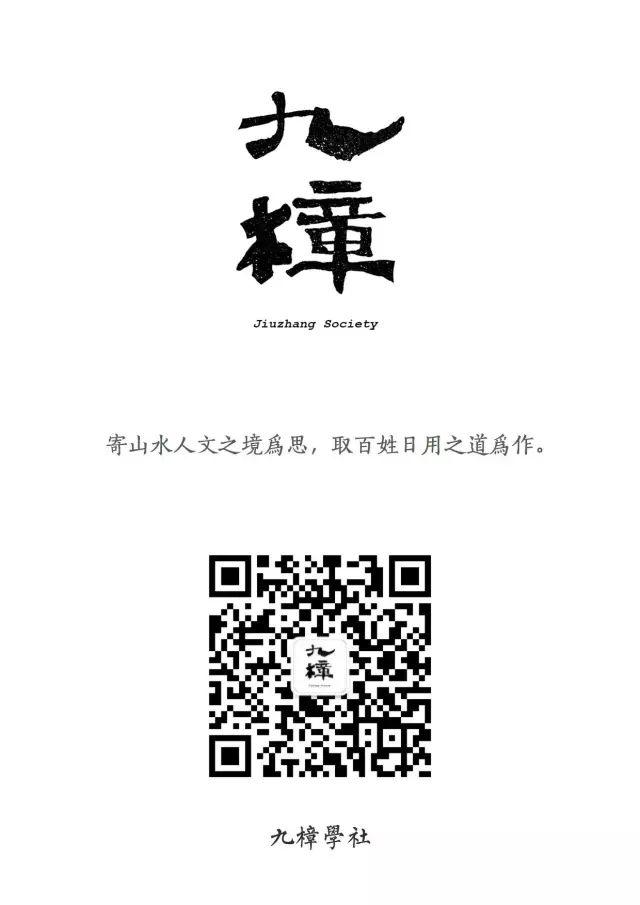▼
一
十一后的秋日,天色沉郁,前往探访大舍新近落成的作品:边园。
从地铁四号线杨树浦路站下来,进入滨江的步行道,漫长的行走,来到越发荒僻的区域。绕过一片芒草织成的景观区,方才见到边园的面貌。
柳亦春先生言道,起名为“边园”便是因为其地处杨浦区的边缘地带。
相较于自我封闭的建筑物,边园更像是一处架构体。场地上原本就存在的旧墙支撑着漂浮的结构,屋面的倾斜赋予两侧以不同的尺度,一体两面,一侧逼向临近的防护墙、形成一处内部的景园;另一侧被轻盈地架起、形成一条挑高的长廊并于尽头收拢为一座亭台。注1
注1:由居中的墙体将纵向空间分割成两片的操作可与苏州园林里常见的复廊体系相比较,但是复廊两侧空间的内/外属性并不总是明晰的,甚至是含糊而难以界定的。
进门后两次折向迎来一条笔直的长道,墙体上出现一个大开口连通着旧墙外侧的旱冰场,前方有一部向上的阶梯,我并没有选择就此上梯或者转出去面向江景,而是继续前行。
两道墙体之间留出的宽度并不富余,长道旁紧邻着被护栏隔开的景观,向上延展的树木隐约覆盖着限定出的视觉领域。屋面向下倾斜,这进一步压缩了我与景观的距离,树木也就愈发显得高耸,根植的土壤起伏着,近护栏处凹陷如谷、堆叠着边缘残破的混凝土块,流成一条石溪、一派山野气息。
旧墙与屋顶之间脱开、形成一道窄缝,外侧的明亮因着金属材质的漫反射而被引入。暧昧的光泽于屋面上晕淡开来,与精心设计的景观共同营造了一种幽冥的氛围。而绿意溢入我的周边视觉并不断蔓延,诱惑着我转过身去、倚撑着纤细的黑色栏杆以顾盼嗅闻。
行路过半,尽头处的光亮愈发明显、近旁的绿意也在褪去。土壤倾斜着浸入江水、大块的混凝土积压其上。江面被风吹荡着,回转去的波浪又与迎面而来的后者击打着,形成震荡的波纹。江水拍击防护墙的声响由弱变强,旧墙的延展随之结束、视野也因之开阔。
阶梯旁的旧墙被敲去大半,于举步向上的过程之中,视线得以与内侧的景园有所联系。
挑高的长廊由锚固于旧墙上的结构轻盈地架出去,成列的细柱支撑起屋面、也拓展了纵向的进深。而于此时,旧墙与屋顶之间的间隙则起到将下方的景观延展上来的作用,水面的波纹被微妙地反映到屋面之上,江水拍打防护墙的声响依然传递着,隔绝了视觉形象的水声更添了一种诱惑力、将思绪推向遥远的地方。
再往前去,屋面映照着的景色被模糊的绿意所替代,行至近半,忽然大片地蔓延开来。中段的墙体被敲去部分以安置座椅,面前是表面粗糙的旱冰场、于水平向延展的线型景观、阔远的江水延绵着隔岸的高楼。而扭转头去,手臂跨置于护栏之上往下探看,倾覆的屋面斜切出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观。
至尽头处,屋面掀起一角,接上平顶而开敞的亭台,面向开阔江景的同时也遥望着远处的杨浦大桥,一位游人在此反复地踱步。亭台端头向内部延出一条横向步道(步道下则是边园入口)连接下行的缓坡(暂未开放),扭转的屋面覆盖着前述开端所见之阶梯,信步而下,绿意便又开始蔓延,两次转向将景观留在身后。
面向旧墙敲出的大开口,孩童于旱冰场上欢闹的身姿以及远方汽鸣的轮船将我从边园中带离。注2
注2:上述描写仅为展现我的一次游走过程,盼借此次体验的叙述对于边园有所展示而非寓意游览路径的固定。正如Yehuda Safran认识到的,“这里既可以呆坐一下午,也可以快速穿越,给人一种自由、闲散,可以闲逛的感觉”,前后两处端口加上旧墙上敲出的大开口、两部联系上下的阶梯以及暂未开放的坡道足以提供给游者多样的移动选择。
于过往的园林分析中,苏州园林的组织结构被固定地简化为观赏路线—观赏点—观赏路线的“系统化构图问题”,但是相较于一种简洁的树状结构,苏州园林显然更偏向于“自然城市”的半网络结构。注3
注3:柄谷行人的解释是,“因为树状结构提供了将复杂事物分割为单元的简单、明晰的方法,所以尽管自然结构总是半网络结构,但人们往往将其还原为树状结构。”
柳亦春先生将作为素材的苏州园林约略为明晰的线性组织,不妨借用瓦莱里的一句表述来对此做解释,人类制造物的特征是,其形态结构要比素材结构简单,但是并不能将游园的过程解释为一种持续运动着的线性过程,被编排为纵长的空间实是一处被体验着的场所而非仅为一道线性的路径,看似于时间线上连续的游园过程事实上是被随机拆解着的,重点在于当下体验的鲜活所带来的吸引而使得“游”这一过程的片段化。
例举而言,漫步于内侧景园之时,我会被眼前的绿意吸引而驻足观看风吹动树叶的姿态、又或者沉浸于江面上震荡的波纹;而移位至挑高的长廊,登高望远的状态使得游者内心的思绪被激发出来、又或者会为旱冰场上嬉戏的身姿所吸引。这些不连续而偶得的片刻的存在使得游园过程不经意地停滞而自发重组。注4
注4:令我感到缺憾的是内部景观与游者之间被护栏隔离着,“香寻石上蒲”的山野寻游的意趣被贬抑、可能深入的移动以及互动体验被压缩。而从边园入口进入,虽可从旧墙的洞口处转出又或者沿着阶梯直上到二层的亭台,但如若选择继续前行,就没有半途抽离的可能性,设计者也并未于内部景园的路途中设置座椅以供休憩,然而,事实上,内向的静谧景园正适合作为私密交流的场所。
柳亦春先生与评论家Yehuda Safra对于边园的英文命名有所讨论,经过一系列罗选,最终选定为“Riverside Passage”,水边的长廊。如果说passage定义了游者身处其间的自在移动以及空间层面的组织结构,那么riverside则给出了边园的地点属性,不过我以为,它其实掌控着更广阔的领域。
就如柳亦春先生叙述的一次场景,廊上的妈妈正微笑着看着在溜冰场上溜冰的孩子。这极有说服力地阐述了挑高的长廊与面前的旱冰场的紧密关联。
可以与之作比较的是葡萄牙建筑师塔沃拉的一处设计,房子处于一片公园之内,由上下两层构成:下层是封闭的供运动员使用的更衣室、上层则是开敞的由单坡顶限定的观演台。kirk老师这样表述道,“应该了解这座网球场附属亭不是一座超脱的建筑,…这座建筑与其说是一座看台,倒不如说是一座主席台,让网球场附属与它,而不是倒过来……”。注5
挑高的长廊将观察者的身体带离地面、而轻盈地架出去的姿态强化了一种脱离感,这一感受调整了具体的人与大地的关系(可以想象,这完全不同于站立与地面之时感受到的被包裹似的知觉),这一关系叠加到视线层面的交错,就如前述于上观察的母亲以及于下玩耍的孩子,这一审视的姿态建立起母亲与孩子之间等级上的差别,这一差别天然地被空间所继承,长廊的领域此时向外扩散着、掌控了其下的旱冰场,同时连接更远处的江景结合为一处更新了的场所体系(于尽头的亭台处更是如此)。注6
https://www.douban.com/note/586035329/。
注6:让我不能理解的是旱冰场与江水之间的景观设计,事实上,我以为不如放置一处完整的退台式看台更能增补场所感,此处的设计包含了较多的内容,因而变得表意不明并自我封闭,具体的使用者往往只会于最高处的线型走道游走一次,这种使用的可能性弱化了双向的围合。
作为废弃物的旧墙此时也重新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不再是柳亦春先生最初见到的埋没于大地之中的孤独设立,对内封闭着静谧的景园、对外则成为旱冰场的边界,墙体本有的界域属性(以及结构属性)被重新激发出来,投入到更新了的场所体系之中。
三
柳亦春先生于近来的演讲中有意引入了《园冶》里的论说以梳理自己的设计理念,“巧于因借、得体合宜”。我借用童明先生将童寯老的“三境界”论解释为一种递进关系的思路将合宜看作为建筑师所追求的目的,而因借与得体则是通向它的两处步序。
因与借蕴含着建筑师对于场地条件的自主判断,这些或是理性或是感性的认知生成了确立建筑与环境关联的结构(得体),设计者于此摒弃了肥腴而意义不明的形式,只留下精简的修辞以作为缠绕于骨架之上帮助体系运转的筋肉与经络,这一判断标准,就如柳亦春先生表述的,“在这里,人会被景观吸引,而不是关注建筑本身,从而这个建筑的‘体’,仿佛就融化在这一片场所里”(合宜)。
我并不欣赏“融化”所暗含的有关同一性的表达,场所体系中的参与物都有着自主的存在感,建筑师建立起来的关系结构精确地介入环境并激发着场地的潜能,但是并不直接灌输内容,骨骼之间的填充物实质上因着游者的具体存在而自发生成,模糊而多样,这也是大舍的这件作品最吸引我的地方。
 最后的回望
最后的回望
《柳亦春&周榕:体-现,潜力的外化》,观点view
《重新理解“因借体宜”——黄浦江畔几个工业场址改造设计的自我辨析》,柳亦春
-End-
编辑:树下小人
九樟学社编辑部
| 版权声明 |
本文版权归九樟学社所有
| 联系邮箱 |
jiuzhangsociety@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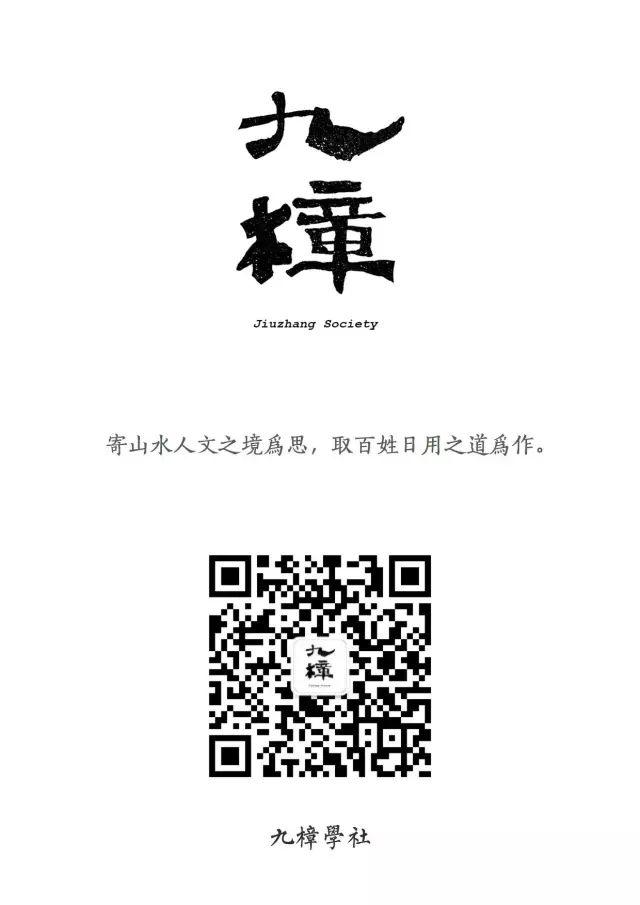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九樟学社):访边园后记











 最后的回望
最后的回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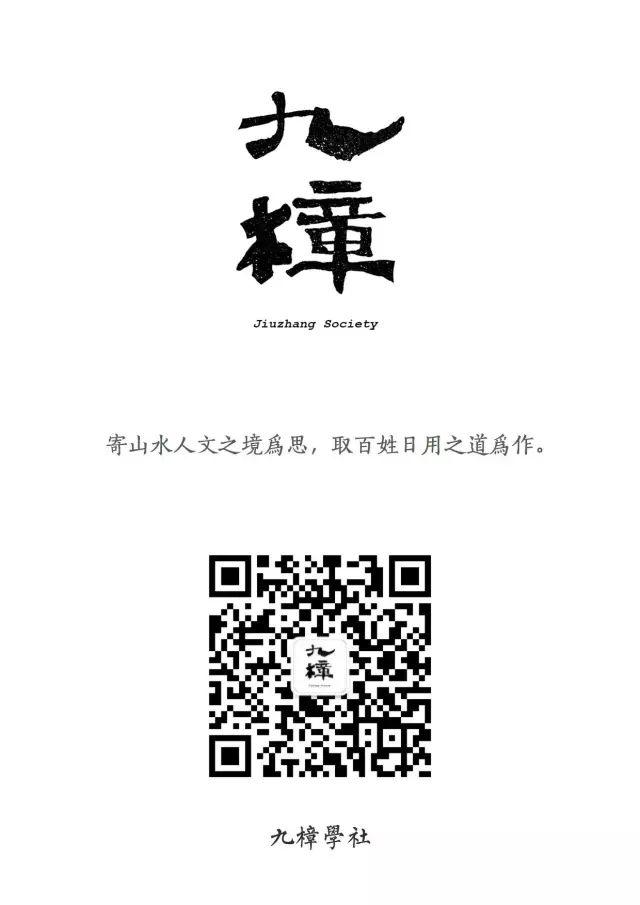











 最后的回望
最后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