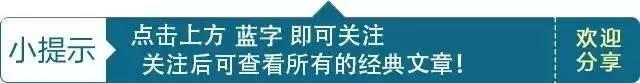
探寻散逸民间的乡音故事;
触摸谆谆流传的乡土人情;
述绘咱厝咱人的心乡映像;
荡开游子家人的乡愁涟漪;
记忆你、我还有他们曾经的故事

古村是指福林古村,新发现,也谈不上,因为又不是新发生的事物,尚属于旧事物,说是“新发现”,应该是相对我这个外来人而言吧。
自从搭上古村落保护以来,特别是今年,差不多每天,我都腻在福林村庄里。有事没事,在村中的老房子里瞎转悠,村里很多老少认识我,经常主动、热情与我打招呼,仿佛我就是邻家兄弟。参观老房子,那些房东竟能让我在里面自由地左瞧瞧,右啾啾,对我也毫不防备,住在书投楼的许先生一家更是经常被我或我带来的访客所打扰,长时间不厌其烦,还是能热情地接待,并经常提供免费的茶水,让我汗颜不已。
在福林古村,传统官式老房子中,保存比较好的就属“下大厝”和“书投楼”,这些老房子里面的一些老物什藏于民众之间,日常生活里,习惯了,便普通了,便不觉得其贵重、特别了。
在下大厝(又称麟族堂)的正厅上挂着一幅画,画上是旅菲的乡人许逊沁(公元1808年–1870年)一家。画中许逊沁正值壮年,头戴红缨斗笠帽,身黑色马褂打扮,意气风发;两个小男孩,一个10岁许,另一个16岁许,身着西服;左边是一个雍容华贵的妇人(应是许逊沁夫人),两个女孩在两旁,也是西式打扮。
认真一看,这幅画是幅油画。我问过村中很多老人,这副画成作于何时,那些老人只是告诉我,这幅画在他们孩时记事时就已经挂在那里了,是百年古画了。我去找耆老许天化先生,这个年近九旬老人,人称村中老知事、活化石。在讨论此事时,他告诉我,据传许逊沁在菲律宾时曾娶一位“番仔婆”为妻,生育了两个男孩、两个女孩。1850年后归国后又娶妻,并又养育了六个男孩。这幅画反映应该是与菲律宾籍妻子及其孩子一家人的生活场景吧。
许逊沁从菲律宾归国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大乡绅,咸丰二年壬子年(1850年)捐助养生堂(安海育婴堂),泉州正堂嘉立“诚心保赤”巨匾,并附时之所兴,曾向清政府捐官,为翰林院主簿。按画中的年龄估算,这幅画应该是许逊沁回国不久后请画匠所绘。
那估算这幅油画应该成品于1850年—1860年之间。
这幅画本就是实打实的古画了,百年古画虽不是罕品。问题是这幅是油画,不是传统的国画,翻翻中国油画史,最初把油画介绍到东方中国的,应该是康熙年间来中国的著名的西方传教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来华后,他成为宫廷御画师,顺便把油画技法介绍给中国,自己作品却慢慢汉化。雍正、乾隆年间,宫廷的包衣(满语即奴仆)受命于皇上,向传教士学习油画,据了解,并未留下一些痕迹。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西文化大碰撞,画坊、画馆开始兴起,画技亦得到了改善,但是当时油画依然并不为普通大众所待见,走入民间甚难。
戊戌变法后(又称百日维新,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许多青年学子先后赴英﹑法、日本等国学习西洋油画,他们中有:李铁夫﹑冯钢百﹑李毅士﹑李叔同(弘一法师)﹑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潘玉良﹑庞薰琴﹑常书鸿﹑吴大羽﹑唐一禾﹑陈抱一﹑关良﹑王悦之﹑卫天霖﹑许幸之﹑倪贻德﹑丁衍庸等。他们这一批人才从西方回来,油画才在中国开启了新的篇章。
这幅画估计成品于鸦片战争和戊戌变法之间。当时中国能以油画者有几人?能把作品流传下来又有几幅?询油画业内人士得知:早期油画者不像国画作者在图中题款、标识日期,可能把名字、时间隐藏在图中细微处,不易被人发现。小编无从辨识,更不善于书画,但如按本人推断属实,以历史的定位中,自认为,此画在中国油画史上可称是殿堂级的文史佐证。
一句话:这是一幅罕见的书画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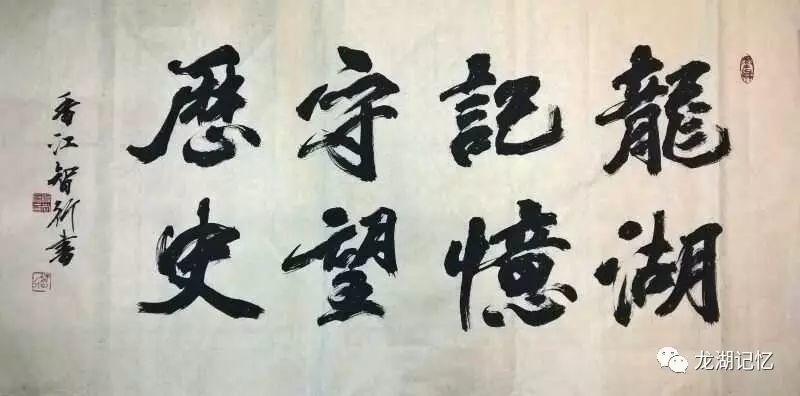
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龙湖记忆
 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