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文章首先简要回顾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城市研究提供的有效和可塑的工具箱,为新的研究分析方式提供了广泛视角。这些视角为彻底关系式和对称式地理解城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它们以不同方式去中心化城市理念和研究。打开城市研究的行动者网络工具箱不仅提出了研究问题的新路径,同时也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相互影响提供了新的跨学科空间。文章进一步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动摇了将城市视为有界稳定实体的单一假设,其在本体论立场上整体改变了城市研究的基础。基于此,文章批判了芝加哥学派、韦伯、齐美尔三种主要城市研究传统,并提出另一种城市本体论,即城市不是被社会建构的,而是由身体、物质、技术、物品、自然和人类组成的网络演成的。因此,城市作为多元物体,来自于城市组装的复数形式涌现。
我们或许正面临着城市研究中的“塔尔德时刻”(Tardean Moment)【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1843—1904 年),法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犯罪学家,与孔德(Auguste Comte)、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一起被视作法国社会学的创始人。涂尔干理论赋予社会“有机体”实体形象。与之不同,塔尔德认为“社会”绝不是某个特定的实体化领域,而是某种联结,是一种循环的流动。塔尔德的社会哲学思想影响了德勒兹(Gilles Deleuze)、瓜塔里(Félix Guattari)、拉图尔等。拉图尔称塔尔德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之父。——译者注】。无数细小的、横向的、几乎边缘性的变化、微小的运动和微妙的迁移正在发生,它们可能突然获得动力,打破模仿性重复的潮流,彻底改变场域。这种情况尚未发生,我们当然无从知晓其可能性,但探索这些微小且微妙的迁移可以揭示令人惊讶的趋势。事实上,城市研究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用关系的、对称的【“对称”(symmetrical)指“(广义)对称性”原则。卡隆(Michel Callon)、拉图尔等为解决科学哲学家面对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真实存在的差异解释能力不足,提出了“广义对称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generalized symmetry)。一般认为,这一原则在本体论上抹杀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差别,但其实质内涵是要求“人类学家必须将自己摆在中点的位置,从而可以同时追踪非人类和人类属性的归属”。所谓中点指拟客体,是指人与物之间的一种杂合体,处于自然和社会两极的中间,自然和社会仅仅是人类赋予拟客体以秩序之后的结果。参见刘鹏. 译者前言:拉图尔哲学的人类学特质[M] // 布鲁诺·拉图尔. 我们从未现代过:对此性人类学论集. 刘鹏, 安涅思,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liv。——译者注】,甚至扁平的【 “扁平”(flat)意指现代哲学中出现的一种新型本体论,即扁平的本体论(flat ontology)。——译者注】视角来理解城市、城市现象和转变,挑战对其研究对象(object)【object 有客体、对象、物体多层含义,其在文中一语双关,既指城市研究的对象,也指城市这一物体。为行文简便,本文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之译为“物体”,有时会根据上下文将之译为“对象”。——译者注】的传统理解。尽管我们肯定无法给出确切数字,但已经有了一些杰出的作品(特别是阿明和斯里夫特[Amin &Thrift] 2002 年的著作【参见AMIN A, THRIFT N. Cities: reimagining the urban[M]. London: Cambridge, 2002.——译者注】)。这些著作不仅改变了词汇,还发现了新的环境和研究和对象。当以对称的和彻底的关系视角去审视城市和都市,确实会发现它们大不相同。但究竟有多大不同,我们仍无法完全预见,而这正是本书这一集结了城市研究新鲜成果的著作所试图探索的。
这本书的探索非常必要,超越了仍然在影响大多数城市研究的强大结构主义范式。至少可以说,将发生在197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断定为城市研究的最后一轮重大理论飞跃是令人担忧的。从全球城市网络到尺度结构化,再到符号和创意经济的概念,这一强大的范式仍然是城市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方法和问题的基础。坚持这种相当过时的范式其实会带来各种风险:用结构变化的元叙事来解释城市生活,无视我们实际生活的复杂多元的城市,与当代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脱节。这本书探讨了斯里夫特(Nigel Thrift)[1]15 提出的“城市僵局”的出路。它既不是对新城市研究形式的呼吁,也不要求有新的读者。不如说,它是获取城市新见解的一种探索,这些新见解来自大胆使用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从事城市研究后的成果。这种背景下,一个紧迫的问题当然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Actor Network Theory)(以及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发展和讨论)将如何改变城市研究。
这本书中还有一些海德格尔式的特点,因为问题本身才是关键所在。因此,正是它的术语(名词而非动词)本身需要仔细评估。书中的大多数作者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ANT这一行动者的构成、实力和禀赋进行了评估(评估后认为ANT可以对城市研究起作用,甚至改变城市研究),并且或多或少对当前城市研究的状态、惯例和盲点进行了批判性诊断。因此,这本书不仅是利用ANT提供的工具探索城市、城市生活、空间和集体的首次集体实验,也是ANT和城市研究这个组合接受检验、测试并最终重新定义的实验。
现在,在解释这本书的三个部分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这样组装前,我想先向读者介绍ANT为城市研究提供的一些工具,并讨论ANT如何对城市研究提出了挑战。总的挑战是——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应该明晰——影响了大多数城市研究对城市的稳定和有界的理解。复数形式的城市组装概念为重新理解城市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将城市视为一个在城市实践的具体地点被不间断组装的物体,换句话说,将其视为一个生成(becoming)过程、黏附着社会技术网络、混杂集体和另类拓扑的多元体(multiplicity)。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变成了难解的、去中心化的对象,不能被想当然地视为有界物体、特定的环境或划界的场地。相反,城市是一种相当奇异的本体论成就,需要加以阐释。
拉图尔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一标签的立场不断转变:先是将其切成碎片[2],后又为其辩护[3]。这表明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定义明确的对象。ANT是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缩略词,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但被更多人务实地用来快速表达他们对所参与的特定类型研究的理解,有时甚至会予以赞美。无论如何,当合成词“行动者网络”和“理论”概念被联合起来,我们会非常谨慎地进行表述,并辅之以对其实际含义的进一步定义:联结(association)研究、对称视角、社会技术分析等。
由此可见,与其说ANT是一个定义精确的问题,不如说是研究者调查和感兴趣的对象,以及对他们所从事研究和讨论(所谓)的共同理解。将其定义为一种理论并不准确,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任何特定的事态提供解释性的理论架构。更确切地说,其涉及对非人类行动者在世界组装中的积极作用、对对象关系构成的某种感性认识,以及对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对称解释的理解。关于ANT参与世界和研究的模式已有很多论述,我们可以补充的不多[3-5],但让我们回顾一下三个核心原则:彻底的关系性、广义的对称性和联结。
众所周知,ANT所做的首先是将关系性原则扩展到语言(如索绪尔[Saussure])、文化(如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和交流(如卢曼[Luhmann])之外的所有实体,因此它具有彻底性。物体、工具、技术、文本、公式、制度和人类不再被认为属于不同的、不可通约的(符号学)领域,而是相互构成的[6]。卡隆(Callon)[7]将维持这种彻底关系的方法论原则称为“广义对称性原则”,主张使用一种共同的概念剧目来描述和分析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现在,揭示参与社会的行动素(actant)的混合链条并不是为了解构社会,而是为了理解构成社会的联结。因此,社会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关系类型,更确切地说是事物之间的联结,而这些事物本身并不具有社会性[3]。这三个一般原则也作为更广泛理论和研究的传义【传义(intermediaries)与转义(mediator)是拉图尔ANT 的重要概念,他曾在《再组装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介绍》(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一书中对两者的意义作了简要区分。“传义是指不经过转换就能传递意义或力量的东西:定义它的输入就足以定义它的输出……传义可以被视为且只能算一个黑盒子,即使它内部有许多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转义不能算‘一个’,它们可以是一,可以是零,也可以是无穷;它们的输入从来不能很好地预测它们的输出;每次都必须考虑它们的特性。转义转变、转译、扭曲、修改意义或它们所携带的元素。无论传义多复杂,出于实际目的,它只可以算‘一个’,或甚至什么都不是,因为它很容易被遗忘。无论转义看起来多简单,它都可能变得很复杂;它可能会导致多个方向,这将修改所有归因于其作用的矛盾说法。”参见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9.】,提供持续的外溢。因此,ANT是一个理论、概念和研究的大杂烩,不断被框定、溢出和重构。作为对研究和世界的感性认识,人们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在ANT背后,多元的理论线索在偷偷地发挥作用,有时会将城市研究的重塑推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人们不禁要问:在ANT这个“开放的建造场地”[4]65 中,哪些材料、工人、承包商、机器和工程师与重塑城市研究尤为相关?
首先要说明的是,突出非人类积极作用的特点使ANT能够建立多元联系,甚至将科学技术研究(STS: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领域内的不同传统纳入其中并加以引导。关注这些相互联系非常关键,因为事实上,把城市理解为社会技术系统和巨大的人工制品,最初是由历史学家和技术社会学家提出的,他们研究大型技术系统[8-10]和技术的社会建构[11]。其中两个颇具影响力的例子是休斯(Thomas Hughes)[9]对西方大都市电气化的研究,以及艾瓦尔和比克(Aibar & Bijker)[12]对城镇规划的研究,两个例子中的技术都是由不同的行动者群体制定和协商,同时衔接了城市的物质和社会部分。
实际上,在其著作《分裂城市主义》(Splintering Urbanism,2001)中,格雷厄姆和马文(Graham & Marvin)作出了重要尝试——将这些视角与ANT的城市视角相结合。他们将城市理解为技术和社会层面组装在一起的过程。即便库塔德和居伊(Coutard & Guy)[13]公正批评了此书在其普遍危言耸听中表现出来的软性技术决定论,格雷厄姆和马文的初步理解仍然是影响ANT城市研究的主要理论线索。格雷厄姆(Graham)的最新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对于揭示城市研究中被忽视的城市进程具有巨大潜力。他对城市战争策略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城市基础设施对城市和公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14-16]。与之相同,格雷厄姆和斯里夫特(Graham &Thrift)[17]探讨的城市维护和修复问题也具有高度政治性。尤其是维护和修复政治与获取、处置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联系,已成为今天地缘政治斗争和环境政治的一个主要议题。
除了将城市作为一个“机械界”(mechanosphere)[18]78 【 该概念源自德勒兹与瓜塔里合著的《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阿明与斯里夫特在其2002 年合著的《城市:重新想象都市》(Cities: Reimaging the Urban)一书的第4 章“机器城市”开头提出:“构建新的社会空间语汇的第一步是将城市理解为一台机器。但在本章中,我们使用这个术语并不是指城市可以通过机器隐喻来理解——有输入、机制和输出——而是作为‘机械界’,一套不断进化的系统和网络,机械组装,混合了诸如生物、技术、社会、经济等范畴,范畴之间的意义和实践的边界总是在变化。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这一概念有个关键结果:技术不能被视为与社会、自然相分离。”参见AMIN A, THRIFT N. Cities: reimaging the Urban[M]. Cambridge: Polity, 2002: 78. ——译者注】,ANT鼓励城市学者研究和反思城市的建筑和建成环境及其生产,并为他们提供了相关工具。事实上,受ANT启发的建筑实践研究取得了巨大发展,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布莱恩(David Brian)[19]可能是第一个将建筑师描述为以工程师—社会学家方式理解事物的人。此外,卡隆[20]对建筑概念和投影工作的反思鲜为人知,但这对于建筑师工作室进行的“异质工程”[21-22]工作和物理模型、透视图、3D计算机设计程序作用等新研究方向的开拓至关重要[23-26]。内夫(Gina Neff)及其同事[27]目前的研究发现,虚拟三维建筑模型引发了建筑师、建筑商与工程师之间的认知不协调和不稳定的合作。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建筑不是静态的物体,而是“移动的项目”[28],在建造时当然也不会停止移动。居伊(Simon Guy)、苏德斯托姆(Ola Söderström)、布兰德(Ralf Brand)等的研究也强调了后一点。建成环境和社会的动态共同发展是他们在可持续建筑[29]、可持续流动性[30]和建成环境的转义作用等问题上的创新工作的核心。
只要一小步,就可以将所有这些ANT影响下的思维观点与近年来城市研究中经常听到的“赛博城市化”(Cyborg Urbanization)概念[31](早期的例子是斯温格杜[Erik Swyngedouw, 1996])分开。即便“赛博城市化”的使用略受技术驱动[32-33],但这一概念引入了两个细微差别,即通过ANT的视角观察城市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至少自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A Manifesto for Cyborg)一书出版以来,作为“生物体和机器组成的混合造物”[34]1,赛博格(Cyborg)的概念主要涉及对一般人类“本性”概念的挑战。因此,“赛博城市化”将注意焦点从作为社会技术系统和巨大装置的城市,转移到这些具有人类特征的混合形式上,即通过技术网络和生命支持系统塑造城市公共领域和体验城市的混合形式。希尔兹(Rob Shields)[35]关于“赛博格漫游者”(Flânerie for Cyborgs)的讨论表明【漫游者(Flânerie)是西方城市研究和现代文学著名的意象,源于法国文学家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诗作,描述了出现在19 世纪经历现代化历程的巴黎中的一群无所事事、终日闲逛的人。这个意象后来在城市研究中反复出现,例如本雅明的《拱廊计划》。——译者注】,赛博格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戴假肢的身体,而是像漫游者一样,关系性地出现在具体的行动场所中,如家庭、市场、工作场所、国家、学校、医院、教堂以及网络这样的电子空间。因此,城市构成了特别有强度的赛博化场所,在这里,多元的赛博格式存在与赛博格式实践绑定在一起。关于赛博格式的城市公共领域,吉拉德和斯塔克(Girard & Stark)[36]对“9·11”事件之后纽约市公共集会的社会技术研究颇具启发性。该研究表明,城市公众的形成由多元社会技术装备促成,而非公共对话的城市领域,这些社会技术装备对于感知与体验、意义构建与想象、采取行动与示威是必需的。
“赛博城市化”概念开启的第二条研究和思考途径涉及城市自然和城市政治生态的作用。ANT强调自然、生态甚至动物行为的能动性(agency),这种强调可以追溯到拉图尔[37]和卡隆[7]分别对微生物和扇贝的经典研究,它不仅激发了学者对城市自然的关注,而且使得城市研究领域内外有了多元联系和盟友。这一领域的先锋无疑是斯温格杜[38]——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城市的生态政治及其与城市化、现代化、尺度政治、社会正义等城市研究核心问题的复杂关系。另一个有趣的先驱是克罗农(William Cronon),他对于芝加哥发展路径的自然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1991年)。该研究已成为ANT学者们称赞的杰作,因为它在解释一个大都会的渐进构成时,并未诉诸社会环境的能动性和其他变幻莫测的动因。还有一个合适的例子是德兰达(Manuel DeLanda)的历史哲学研究[39]——讨论了地质和生物过程在世界历史,特别是城市历史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现在回到上文提到的公众集会问题,所有这些元素都使得一个问题变得尤为紧迫:事物和生命形式的议会是否可行以及如何可行[40]。在城市研究中还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可以在法律研究关于非人类权利的一些最新讨论中找到很好的切入点[41]。
综上所述,人们应当注意到ANT涉及的不仅仅是对城市研究中没有考虑到的维度和因素的开放。其狂热的反结构主义立场,以及对现实地点和活动线的强大经验投入,使其成为对其他广泛被运用和接受的特性、对正在起作用的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和解释模式的重大挑战。这影响到城市研究中的感觉的(sensible)问题,如空间的生产或城市经济的动态。事实上,ANT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解释——将空间和时间视为构成行动者网络的关系和联结的结果、影响甚至因变量。从这个角度来看,空间并不是由资本关系[42]、国家战略[43]或其他因素产生的底层结构【此处暗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经典的结构化论断的批评。——译者注】。将空间和尺度看作产物,使其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生产它的一系列实践(结构化的最终含义),这样的思维模式会陷入拜物教陷阱——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将特定行动者网络与城市场地的属性视为真实的、本体论上自主的东西。更确切地说,空间、尺度和时间在具体的地方被多元地演成(enact)和组合,具体的行动者以各种方式塑造时空动态,从而生产不同的联结地理。
这种对现实和具体城市场地的经验投入,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拉图尔和赫曼特(Latour & Hermant)马赛克式的作品《看不见的巴黎》(Paris Ville Invisible)[44]。这本书表明巴黎不存在于某个空间或尺度,而是在多元地点以不同方式演成。空间、时间和城市本身被生产,或者更确切地说,其涌现被在局部场地运转的行动者网络的类型和延展所调节。ANT以这种方式动摇了城市研究赋予空间的自主性和解释上的优先性,以复数形式场地这一关键概念取而代之。场地不是由空间边界或尺度定义的,而是由活动的类型和线索定义,空间从连接不同场地的网络中涌现[45]。因此,当ANT成为一种松散耦合的媒介,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和非表征主义(non-representationalist)[46]的空间概念通过这一媒介影响城市研究,都对城市研究中通常提及的空间形构(spatial formation)提出了挑战与反对,无论是全球运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还是地方整合的城市生产集群。
由此可见,ANT同时提供了对城市经济动态的新见解。ANT转向经济研究主要是通过卡隆[47]对经济学述行性(performativity)的开创性考察,以及由此提出的对经典的“新经济社会学”的挑战[48]实现。卡隆认为,经济行动并不嵌入社会网络(城市社会学和经济地理学乐于将其理解为沉淀于城市空间集群),但它是被框定的活动(framed activity),其发生需要脱离社会。因此,如果说经济行动嵌入了什么之中,那就是嵌入了通过知识和手段执行(perform)市场活动的经济学之中。这种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人类学和社会学,其根本之处在于超越嵌入性范式[49-50]的城市经济研究新方法成为必需,并渗透进全球城市[51]、创意经济[52]等问题的讨论中。众所周知,阿明和斯里夫特曾尝试过这种新方法。在《城市:重新构想城市》(Cities: Reimagining the Urban)[18]一书中,他们提出将城市经济角色看作聚合需求的催化剂,这是一项重要转变。生产集群从当地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的观点受到质疑,城市作为经济生产单位的概念也随之受到质疑。城市的经济作用在于其需求效应。因此,一种新的“后制度主义”观点得以实施,它强调城市制度作为需求集聚实例,而非监管机器的作用。
ANT重塑了我们对城市基础设施、建成环境、生态、城市居民、实践、空间、经济和其他城市研究核心问题的看法,最终涉及对城市本体论地位的经验和哲学研究。实际上,尽管ANT一开始研究的是实验室中的知识制造,并因此处于“科学战争”【指发生于1990 年代美国科学实在论者与后结构主义评论者之间一系列关于科学理论本质的争论。物理学家索卡尔(Alan Sokal)炮制的“索卡尔事件”(Sokal Affair)成为科学战争的代表。——译者注】的核心,但其并非简单地重塑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地位,而是将这些知识的生产理解为一种以实践为根基的本体论成就。从这些角度来看,认为城市的本体论地位在此正处在危急关头,并不意味着同意以下观点,即科学技术研究(STS)中的本体论转向只是最近才出现[53]。至少拉图尔的思想方案一直是关于“实存模式(the modes of existence)的系统比较”[28]9,如科学、技术、宗教、法律或政治,它们构成了“欧洲的形而下学(infraphysics)或区域本体论(取决于我们想如何称呼它)”[28]9。这并不新鲜。十年前一件有名的事情是,拉图尔[2]曾提到林奇(Michael Lynch)的建议,即ANT实际上应被称为“行动素—块茎本体论”(actant-rhizome ontology)。这是一个糟糕但准确的术语,它清楚地表明了ANT运作的德勒兹框架。的确,ANT与德勒兹的形而上学有一些共同的核心特征,如柏格森式的概念[54],即实在(reality)是质的多元体(reality is qualitative multiplicity),我将在下一节再谈这一点。除此之外,ANT从德勒兹的创造哲学中衍生出经验的课题,重点关注行动者网络的生成能力,以及新实体(物体、技术、真理、经济行动者)和新维度(时间、空间)的形成。
我们可以不断地指出更多思想脉络和学术传统,并通过ANT指出它们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对城市理论和研究进行去中心化。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明确指出,ANT混杂了各种理论、作者、问题和感受力,严格来说不能充当任何事物的理论。这一我们刚刚揭开的ANT复杂局面,为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当有用且具有可塑性的工具箱,为以新的方式研究城市提供了广泛视角。所有这些视角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对城市进行关联性和对称性的理解:挑战全球与地方、近距离与远距离、内部与外部的区别,挑战场所、邻近和有界概念的区别,不再将社会文化符号、结构或实践置于城市自然、技术基础设施之上,彻底重新思考城市权力和知识的基础以及城市制度的概念,等等。因此,为城市研究打开行动者网络工具箱不仅需要提出研究问题的新方法,而且需要在城市中开展研究的新方法。此外,它也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跨学科空间。
但这当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尤其是没有模板可以机械照搬到城市研究中。事实上,ANT提供给城市学家的许多丰富资源都应首先从其最初发展的复杂社会技术环境中分离出来,并被转译进城市领域——一个更广阔的环境,没有实验室或交易大厅那么壮观,却复杂得多或非常不同。作为创造性和变革性的过程,转译确实是关键所在,因为不仅ANT在转变,城市研究领域本身也在转变。事实上,本书所涉及的进步,即探索ANT如何改变城市研究,以及在接受ANT的挑战之后如何思考城市,不仅证明了ANT的构成和力量,而且对城市研究进行了批判性评估。
城市组装;或去中心化的城市研究对象
如果说ANT对城市研究提出了全面挑战,那么它并不仅仅是我们在上文确定的局部迁移和微妙变化。其实没有必要认为突出城市的社会技术构成比扁平的空间概念更具挑战性,或认为对城市人的赛博式理解比质疑经济生产的城市嵌入性更具突破性。所有这些侧重点都涉及为该领域引入新的讨论和维度的研究途径,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对整个城市研究提出挑战。相反,我们需要确定改变城市研究基础的根本性位迁移,影响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构思方式。事实上,如果说ANT的本体论立场应被归因于任何一个特定事物,那应是它的追踪和概念化对象的人种志方法的强大准确性和分析精巧性。其实,这一点很早以前始于拉图尔和伍尔加(Latour & Woolgar)[55]对不可变移动(immutable mobiles)的探查:尽管在欧几里得空间中发生位移,但物体仍在网络空间中保持稳定的位置并保持不变[56]。而(后)行动者网络的最新发展也与对物体/对象质疑的考察有关,无论是流体技术[57]还是多元身体[58]。
这样的“物体/对象经验”(object lessons)[59]可能与城市研究高度相关,因为即使“城市”的概念在细节上可能有很大差异,但它们仍然是相当单一的假设,即城市(应该)具有某种形态的稳定性,城市是行动或文化的空间形态、社会经济实体或场地,(应该)可以被积极识别和明确地界定。事实上,这个领域对城市概念的固执是惊人的。自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城市规划者早期尝试发展城市研究领域以来,人们一直以高度稳定和有界的方式来理解城市的现实。虽然许多当代研究已经揭示和探索了城市生活的关系或过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被理解为“一个”实体,可以在多元表征和实践语境中被识别、观察和调查。其实,那些看似全新的想象城市及其当代变革方式,例如强调跨越城市边界的联系或批判地评估社会经济分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同样的旧方案中构建的。因此结果是二元对立的:城市是有界的还是碎片化的,是单一的还是双重的,是一个还是多个。
至少有三种对城市的主要理解可以追溯到早期,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城市研究,没有太大变化。概括地说,这些观点涉及将城市理解为空间形态、经济单元和文化形构。当然,这些都不是另类的观点。实际上,很难想象任何有趣的城市研究不是建立在这三个维度与其他维度之间的多元联系之上。然而,出于分析的目的,有必要对这些基本理解进行区分,探讨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趋同于城市构成有界或稳定实体这一假设,无论是空间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实体。
因此,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些众所周知的论点。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城市生态学方法为城市、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动态提供了相当精妙的空间理解。伯吉斯(Burgess)[60]、麦肯齐(McKenzie)[61]和帕克(Park)[62]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城市构成了明确的空间环境。人类城市社区作为生态过程的结果,以清晰可辨的社会空间模式(比如对区位的竞争、入侵、继承等)在其中安居下来。这种视角为邻里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隔离、房地产市场动态和其他城市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和见解;并且为平衡方法、社会区域分析和其他旨在理解社会和经济力量导致的城市内在空间动态和分化的观点提供了基础。但若不考虑这条线索下发展出的非常精巧的模型,被这一视角置于显著地位的是将城市当作空间单位、当作空间限定场所的普遍理解。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常识性城市概念的重要性,特别是在1980 年代,城市形构的研究才变得如此有趣和有吸引力,从而挑战了有界空间的概念[63-64]。索亚(Edward Soja)的“后大都市”概念[65-66]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他在谈到后大都市的空间特征时提到了“外都”(expolis)的扩散:
“一些人把这些无定形的老式郊区称为‘外城’或‘边缘城市’,另一些人则称之为‘技术极’‘技术郊区’‘硅景观’‘后郊区’‘大都会’。我将它们统称为‘外都’,即没有的城市,以强调它们的矛盾歧义,以及它们充满城市的非城市性。这些不仅仅是外围散落的外—城市(exocities),同时也是前—城市(ex-cities),不再是以前的城市了。”[67]238-239 【译文参考: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刘佳林,朱志荣,等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300. ——译者注】
有趣的是,外都与有界城市概念的直接对位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城市与外都、大都市与后大都市都主要被想象成欧几里得空间和几何空间中的物体。
城市研究的另一个传统可以追溯到韦伯(Max Weber)[68]关于城市对资本主义作用的经典研究——将城市理解为一个经济单元,有时甚至是经济行动者,涉及特定形式的政府和城市体制。很早开始,这一概念就极具影响力,特别是当它与更大的地理视角相辅相成,后者将城市理解为更大城市系统中竞争的经济实体。例如: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69]的中心地理论以其开创性网络模型解释了城市的规模、区位、经济发展和专业化,该模型权衡了节点(阈值)及其联系(范围)的质量。实际上,当代关于城市间竞争、城市系统、全球城市以及最近的创意城市的大部分文献,都是以这种将城市理解为经济行动者、行为实体为基础的。马尔库塞(Peter Marcuse)[70]最近指出了这些概念的隐藏内容:
“如果一个城市不参加奥运会,而城市中的某些群体参加,那么其他群体往往会强烈反对参加。这种将城市视为行动者的观点可能是最具政治色彩……(的)用法,因为它意味着城市内部利益的和谐;对一个人(通常是商界)有利的事就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事。”[70]3
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这种用法不仅常见于政治言论。萨森(Saskia Sassen)和其他讨论全球化与城市的学者有时也会陷入这种用法,即“城市将成为新全球经济的主要行动者”[71]14。在这里,城市作为一种不同类型的物体出现,它不是空间物体,而是网络物体,它的形状和位置取决于它与其他网络物体的关系。
将城市描述为全球性、信息性或创造性实体的问题在于提喻(synecdoche),也就是说,将物体的一部分当作物体整体[72]。有趣的是,正确回避提喻和政治正确地确定各部分之间的差异往往导致物体的瓦解。自1980 年代以来,“二元城市”(dual city)[73]和“分裂城市”(divided city)[74]的概念一直被用来强调城市中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即使这些概念因其简单化的分析构念——富人和穷人、全球和地方等——而受到激烈的讨论和批评。替代方案如“碎片城市”(fragmented city)或“碎裂城市”(quartered city),尽管它们涉及对社会空间极化更具体的分析,但它们同样具有分裂城市的基本思想。在这里,城市理论再次陷入了我们上文指出的哈姆雷特困境:如果不将城市视为一个政治经济行动者,它就会被想象为无法聚合在一起。马尔库塞在这方面说得很清楚:“当你把所有(利益)集团放在一起时,你不会得到一个东西,一个‘城市’”[70]5。城市,似乎可以是一个,也可以不是。
有关城市的第三条主要思路可以追溯到齐美尔(Georg Simmel)[75]关于大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开创性文章,帕克(Robert Park)[76-77]将城市理解为一种精神状态,以及沃斯(Louis Wirth)[78]将城市性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作为文化的概念——匿名的、眩晕的、公共的——以及对其不同显现方式进行人种志研究的要求。因此,城市文化被视为城市的构成要素:
“我们通常认为的城市大部分内容——宪章、正式组织、建筑物、街道铁路等等……只有当它们像人类手中的工具一样,通过使用和习惯,与个体和共同体中的生命力相联系时,才有可能成为有生命的城市的一部分。”[76]3
因此,要将城市理解为人类秉性的产物,特别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就必须对城市居民中普遍存在的习俗、信仰、社会实践和一般生活概念进行调查。在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中,邻里(neighbourhoods)是追踪城市文化不同表现方式的关键分析单位。在这里,城市文化作为底层共同基础(underlying common ground),连接着不同城市生境、民族群体和道德领域。在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79]、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80]和德尔加多(Manuel Delgado)[81]等学者有关的日常都市主义传统中,城市文化是从无处不在的城市日常空间中寻找和研究的。在这种背景下,城市文化不是用来帮助理解城市如何在内在差异化的情况下仍能维系在一起,而是用来帮助理解城市作为传播、转变甚至革命的过程。城市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或“一”种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城市区域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涉及城市地区间的创造性运动和不可控空间。城市文化通过残留和短暂的空间得到认可,这些空间甚至被视为与有界场所、固定的意义和庞大的历史所构成的“城市”对立。
将城市视为文化,会引发我们在上述对城市的空间和经济理解中所观察到的同类困境。问题在于物体的稳定性。作为一种文化形构,城市被想象为流动的物体,尽管在不同情况下有细微的变化,但它们仍然是相同的。它们是流动的,因为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却保持着自己的形状和同一。因此,虽然我们可以把许多活跃的欧美城市看作流动的城市文化的类似表达,但一旦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差异过大,我们就会面临悖论,即城市文化无法归属于城市。而这恰恰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作为流动的文化物体,城市要么是流动的城市文化的所在地,要么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秉承日常城市主义传统的学者指出城市与城市生活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德塞托和列斐伏尔的基础上,德尔加多(Delgado)[82]提出了非城市(non-city)这一生成性概念,以理解创造性实践和短暂空间在城市中的不间断的传播。非城市与奥格(Marc Augé)[82]对“非场所”(non-places)的否定性论述并不混淆,它针对的是行人策略、街道舞蹈、冷漠、匿名性和定义城市文化的其他特征,他解释道:
“构成城市的是……非城市,它不是城市的对立面……而是对已形成事物的持续还原,以及对我们眼前正在瓦解事物的无休止重建。”[81]63
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文化虽然不能用于断言所有城市,但它构成了一种无法被任何城市概念固定和稳定的重要力量。
这种粗略的总结无疑是非常基本且不完整的。公平地说,人们可以反对将空间、经济和文化维度笼统地分开,并反对某些隐含的概括。这个领域比这和我们所知道的要更加复杂。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它抓住了城市思想重要分支的基本概念,从而使我们能够进行公平的批评,即城市大多被认为是一个有界单元和一个稳定物体:一个空间形式,一个经济政治实体,一个文化形构。此外,批判性地质疑“一个”城市理念的洞见和概念并没有引发任何根本转变,因为它们太快地转移到二元对立的另一面:城市存在或不存在;它是一个或多个。虽然外都、分裂城市和非城市性的概念摒弃了“一个”单一而综合的城市理念,但它们使这一对象内爆。仅仅探明社会空间的深刻极化和城市文化与城市之间不可逾越的差距,并不会引出对城市这一对象的全新理解,反而往往导致放弃。
ANT方法的主要贡献归根结底在于描述了城市的另一种本体论,给出了对这个混乱而难以捉摸物体的另类理解。这里只是刚开始想象这种另类的本体论。然而,有三个核心原则或概念是坚不可摧的。首先,城市的实存模式与其说是“在那边”(out-thereness)的概念,不如说是“这里面”(in-hereness)的概念。这一原则源于劳(John Law)[83]对于社会科学方法的实在论(realistic)假设的讨论,其中涉及将物体理解为独立实体,甚至先于我们行动,具有明确的边界,并在单一共享实在中构成。劳表明,从很早开始,ANT就通过观察物体是如何在特定实践场所被制造和破坏,来对抗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即便“在那边”也是“这里”(in here)精心制作和生产出来的,因为投入巨大努力是为了使物体获得独立性和预先性,而表征实践被卷入产生确定性的过程。由此可见,城市是具体实践的可变产物,在处境中,在这里建构的。其次,城市不是社会建构的,而是在身体、物质、技术、物体、自然和人的网络中演成的。拉图尔[84]指出,建构概念的基础是强大的造物主的假设,无中生有地(ex nihilo)建构和创造诸如社会、结构、文化、话语的事物。此外,由于实在的建构大多通过认识论术语来理解,参与建构的材料和传义被剥夺了一切主动的角色。我们要如何想象本地构成城市的方式当然不是这样。摩尔(Mol)[57]提出的演成概念能更准确地理解物体是如何形成的。与(主体)述行(performance)的概念类似,城市等物体的演成不仅是社会性的,也是物质的,涉及实践场地和环境中活动实体的异质生态。
由此得出的原则是,城市是多元物体。当然,这一建议立足于摩尔开创性的著作《多元的身体》(The Body Multiple)[57]。她在书中提出,物体(如身体)在不同时刻和地点被演成,演成方式的差异不应在认识论上被理解为关于物体的不同视角,而应从本体论上承认不同实在于这里和那里、此时和彼时被演成出来。这种理解触及柏格森(Bergson)关于实在多元体(the multiplicity of reality)的论断。在柏格森[24]看来,多元体源于真实(the real)的时间性质,或更确切地说,绵延性质,因为正是这种时间维度使潜能的可能性(potential possibilities)和潜在趋势(virtual tendencies)成为物体的基本方面。通过时间和空间,同一物体被证明是多元的。如果这适用于在医院内移动的身体,它当然也适用于在不同地点和时间以多种不同方式演成的城市。阿明和斯里夫特也强调了城市的这一特点,他们认为:
“城市由潜能的和现实的实体/联结/共在(togetherness)组成……这些实体的积累可以生产新的生成——因为它们相遇的方式如此之多,因为它们可被理解的方式如此之多,因为它们表现出“合生性”(concrescence)。”[18]27
在这里,合生性是指城市实体的相遇和联结生产的城市实在涌现,而生成是涌现的过程。现在有趣的是,这些多元演成或多元生成并没有被理解为流动地相互跟随,而是不连续的,甚至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正如摩尔[57]所指出的,它们彼此碰撞、重叠、干扰,从而形成了需要加以管理、协调甚至分开的多元体。因此,将城市理解为多元物体涉及城市研究的一个重大挑战:识别、描述和分析城市的这些多元演成,并理解它们是如何被衔接、隐藏、暴露以及变得在场或不在场[58]。
复数形式的城市组装概念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概念工具,可以将城市当作多元物体来理解,以传达其多元演成的含义。使用这一概念有很多原因。首先,这个术语提供了一个具体和可理解的形象,说明城市是如何在异质的行动者、物质和社会方面的全体中形成并存在的。这种社会物质和社会技术全体的概念是组装最字面的含义。事实上,这是对德勒兹和瓜塔里agencement[85]概念相当不精确的翻译。agencement是法语中相当常用的术语,指不同元素的排列和组合[86]。相应地,它允许并鼓励研究物体、空间、材料、机器、身体、主体性、符号、公式等等之间的异质联系,它们以多元方式“组装”城市:作为旅游城市、交通系统、滑板者和自由奔跑者(跑酷)的游乐场、权力景观、政治行动和示威的公共舞台、禁区、节庆、监控区、社交空间、私人记忆、创意环境、涂鸦与街头艺术家的巨大舞台、消费市场、司法管辖区等等。正如马库斯和萨卡(Marcus & Saka)指出的,组装的概念由此成为社会和文化理论的“主要推力”,聚焦于“当下总在涌现的状况”[87]101-102。它使双重强调成为可能:既强调物质的、现实的和被组装的,也强调涌现的、过程的和多元的。
城市组装的涌现构成表明,实际上它们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多元要素相遇或相加的结果。考虑到agencement 和能动性(agency)两词的共同词源,我们应该注意到,城市组装能够促成新的活动和能动性类型[88]。因此,能动性是组装的一种涌现性能(capacity)。由此,我们转向城市组装的第二个概念。正如德兰达[89]指出的,应从外部性关系来看待agencement 或组装。这意味着异质元素之间的关系(城市组装从中形成)并不一定会改变每个特定元素的特性(identity)。旅游城市组装很可能需要政治建筑、艺术画廊或公共汽车路线的共同参与,但并不一定会改变这些特定实体中的任何一个。组装并不形成定义每个部分的整体或总体性,而更多是涌现的事件或生成。因此,城市组装指的是城市成为房地产市场、电影场景、记忆场所的过程;正是行动或力量导致了城市的特定演成。有趣的是,拉图尔[3]没有使用名词“assemblage”,而是使用动词“assembling”来理解社会是如何通过人类和非人类元素的联结而聚集在一起。社会(the social)、组装的过程外在于这些行动素,它们并没有成为社会,仍然是人、物质的、技术的和生物的。同样,城市组装的概念认为,城市是多元组装过程中涌现的品质,它并不预先存于街道、建筑、人、地图等之中。因此,城市不是在那边的实在,而是由城市组装构成的,通过城市组装,城市以多元方式形成。
与科列尔和翁(Collier & Ong)[90]提出的“全球组装”概念一样,复数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观察到,全球涉及抽象形式,如市场计算。这些形式在复杂的基础设施条件下现实化。因此,全球总是一个现实的全球(an actual global)。这个现实的全球是复数。它不会处处产生类似的效应,其功能和意义可能因其组装的多元规定而大不相同。用我们的话来说,全球是多元的,这种多元体源于潜在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现实的城市,作为全球的城市,只存在于具体的组装之中,并没有为其多元演成提供包罗万象的形式。因此,城市是一个偶然的、情境化、局部的和异质的成就:实际上是一个本体论成就,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原本不实存物体/对象的演成。UPI
参考文献
[1] THRIFT N. An urban impasse?[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993, 10(2):229-238.
[2] LATOUR B. On recalling ANT[M] // LAW J, HASSARD J, eds.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Oxford: Blackwell, 1999: 15-25.
[3]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CALLON M. Actor-Network Theory[M] // SMELSER N, BALTES P, ed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Amsterdam:Pergamon Press, 2001: 62-66.
[5] LAW J, HASSARD J.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M]. Oxford:Blackwell, 1999.
[6] LAW J. Notes on the Theory of the Actor-Network: ordering, strategy, and heterogeneity[J]. 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 research, 1992, 5(4): 379-393.
[7] CALLON 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Brieuc Bay[M] // LAW J, ed. Power,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86: 196-233.
[8] COUTARD O. The governance of large technical system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9] HUGHES T P. 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80-1930[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10] SUMMERTON J, eds. Changing large technical systems[M]. Oxford:Westview Press, 1994.
[11] PINCH T, BIJKER W.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84, 14(3): 399.
[12] AIBAR E, BIJKER W. Constructing a city: the Cerda Plan for the extension of Barcelona[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997, 22(1): 3.
[13] COUTARD O, GUY S. STS and the city: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hope[J].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es, 2007, 32(6): 713.
[14] GRAHAM S. Switching cities off[J]. City, 2005, 9(2): 169-194.
[15] GRAHAM S. Cities and the war on Terro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6a, 30(2): 255-276.
[16] GRAHAM S. Cities, war, and terrorism: towards an urban geopolitics[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6b, 96(1): 216-218.
[17] GRAHAM S, THRIFT N. Out of order: understanding repair and maintenance[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7, 24(3): 1.
[18] AMIN A, THRIFT N. Cities: reimagining the urban[M]. Cambridge, Oxford: Polity, 2002.
[19] BRAIN D. Cultural production as “society in the making”: architecture as an exemplar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rtifacts[M] // CRANE D,e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1994: 191-220.
[20] CALLON M. Le travail de la conception en architecture[J]. Situations: Les Cahiers de la recherche architecturale, 1996, 37(1er trimestre): 25-35.
[21] LAW J. Technology and 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 the case of portuguese expansion[M] // BIJKER W E, HUGHES T P, PINCH T J, et al.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111-134.
[22] LAW J. Notes on the Theory of the Actor-Network: ordering, strategy, and heterogeneity[J]. 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 research, 1992, 5(4): 379-393.
[23] HOUDART S. Des multiples manières d’être réel[J]. Terrain, 2006, 46:107-122.
[24] YANEVA A. A building is a multiverse[M] // LATOUR B, WEIBEL P, eds.Making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530-535.
[25] YANEVA A. Scaling up and down: extraction trial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5b, 35(6): 867.
[26] YANEVA A. How buildings “surprise”: the renovation of the Alte Aula in Vienna[J]. Science studies, 2008, 21: 8-29.
[27] NEFF G, FIORE-SILVAST B, DOSSICK C. Model failure: assemblages,performances, and uneasy collaborations in commercial construction[C]. San Francisco: American Sociological Meetings, 2009.
[28] LATOUR B, YANEVA A. Give me a gun and I will make all buildings move: an ANT’s view of architecture[M] // GEISER R, ed. Explorations in architecture: teaching, design, research. Basel: Birkhäuser, 2008: 80-89.
[29] GUY S, MOORE S A.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s: cultures and natur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M]. New York: Spon Press, 2005.
[30] BRAND R. People plus technology: new approaches to sustainable mobility[J]. Built environment, 2008, 34(2): 133-139.
[31] GANDY M. Cyborg urbanization: complexity and monstro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5, 29(1): 26-49.
[32] MITCHELL W J. Cyborg civics[J]. Harvard architecture review, 1998, 10: 164-175.
[33] MITCHELL W J. Me++: the Cyborg self and the networked city[M]. Cambridge, M.A., London: MIT Press, 2003.
[34] HARAWAY D.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J]. Socialist review, 1985, 80: 65-107.
[35] SHIELDS R. Flânerie for Cyborgs[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6,23(7/8): 209-220.
[36] GIRARD M, STARK D. Socio-technical assemblies: sense-making and demonstration in rebuilding Lower Manhattan[M] // LAZER D, MAYERSCHOENBERGER V, eds. Governance and information: the rewiring of governing and delib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7] LATOUR B.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8] SWYNGEDOUW E. Power, nature, and the city: the conquest of water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urbanization in Guayaquil, Ecuador: 1880-1990P[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7, 29(2): 311-332.
[39] DELANDA M. A thousand years of nonlinear history[M]. New York: Swerve Editions, 2000.
[40] LATOUR B.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1] TEUBNER G. Rights of non-humans? electronic agents and animals as new actors in politics and law[J].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006, 33(4): 497.
[42] SMITH N. Geography,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M] // DOHERTY J, GRAHAM E, MALEK M, et al. eds.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Macmillan, 1992: 57-79.
[43] BRENNER N. New state space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M].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4] LATOUR B, HERMANT E. Paris ville invisible[M].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La Découverte, 1998.
[45]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Clarendon lectures in management studies[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6] THRIFT N.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M]. London: Routledge, 2007.
[47] CALLON M.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markets in economics:introduction[M] // CALLON M, ed. The laws of the market. Oxfor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48] SWEDBERG R. New economic sociology: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what is ahead?[J]. Acta Sociologica, 1997, 40(2): 161.
[49]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50] SASSEN S. The embeddedness of electronic markets: the case of global capital markets[M] // KNORR-CETINA, PREDA K A, eds. The sociology of financial market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37.
[51] 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leisure and everyday life[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52] AMIN A, THRIFT N. Cities: reimagining the urban[M]. Cambridge,Oxford: Polity, 2002.
[53] WOOLGAR S, NEYLAND D, LEZAUN J, et al. A turn to Ontology in STS?ambivalence, multiplicity and deferral[C]. Session in ‘Acting with Science,Technology and Medicine’: Four-Yearly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S) and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ASST), Rotterdam, 2008.
[54] DELEUZE G. Bergsonism[M]. New York: Zone Books, 1988.
[55] LATOUR B, WOOLGAR S.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56] LAW J. On the methods of long-distance control: vessels, navigation and the portuguese route to India[M] // LAW J.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234-263.
[57] DE LAET M, MOL A. The Zimbabwe Pump: mechanics of a fluid technology[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0, 30: 225-263.
[58] MOL A. The body multiple: ontology in medical practice[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9] LAW J, SINGLETON V. Object lessons[J]. Organization. 2005, 12(3): 331-355.
[60] BURGESS E W. The Growth of the city: 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M] // PARK R, BURGESS E W, eds.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u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47-62.
[61] McKENZIE R D. The scope of human ecolog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6, 32: 141-154.
[62] PARK R E. 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gy[M].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2.
[63] FISHMAN R. 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ia[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64] GARREAU J. Edge city: life on the new frontier[M]. New York: Doubleda,1991.
[65] SOJA E. Six discourses on the post-metropolis[M] // Westwood S, Williams J,eds. Imagining cities: scripts, signs and memories. London: Routledge, 1997.
[66] SOJA E.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M]. Oxford: Blackwell, 2000.
[67] SOJA E.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M]. London: Blackwell, 1996.
[68] WEBER M. The city[M].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86.
[69] CHRISTALLER W. Die zentralen Orte in Süddeutschland[M]. Jena: Gustav Fischer, 1933.
[70] MARCUSE P. What is “the” city?[Z]. Unpublished text, Center for Metropolitan Studies,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2006.
[71]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M]. Tokyo,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72] AMIN A, GRAHAM S. The ordinary city[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7, 22: 411-429.
[73] MOLLENKOPF J, CASTELLS M D. City: restructuring New York[M]. New York: Sage, 1991.
[74] FAINSTEIN S S, GORDON I, HARLOE M. Divided ci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M]. Oxford: Blackwell, 1992.
[75] SIMMEL G. Die Gro1234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M] // PETERMANN T, ed. Die Gro1234stadt: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zur Städteausstellung,Dresden: Jahrbuch der Gehe-Stiftung Dresden, 1903: 185-206.
[76] PARK R E.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M] // PARK R E, BURGESS E W, eds. The city:suggestions for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1-46.
[77] PARK R E. The city as a social laboratory[M] // SMITH T V, WHITE L D,eds. Chicago: an experiment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1-19.
[78] WIRTH L.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44(1): 1.
[79]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91.
[80] DE CERTEAU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M].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81] DELGADO M. Sociedades movedizas: Pasos hacia una antropología de las calles[M]. Barcelona: Anagrama, 2007.
[82] AUGÉ M. Non 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hypermodernity[M]. New York: Verso, 1995.
[83] LAW J. After method: mes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M]. London:Routledge, 2004.
[84] LATOUR B. The promises of constructivism[M] // INDE D, SELINGER E, eds. Chasing technoscience: matrix for material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27-46.
[85] DELEUZE G, GUATTARI F. Rhizome[J].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1981, 8: 49-71.
[86] PHILLIPS J. Agencement/Assemblage[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6,23(2/3): 108109.
[87] MARCUS G, SAKA E. Assemblage[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6,23(2/3): 101-106.
[88] MUNIESA F, MILLO Y, CALLON M. An introduction to market devices[M] // CALLON M, MILLO Y, MUNIESA F, et al. eds. Market devices. Malden, M.A., Oxford: Blackwell,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 1-12.
[89] DELANDA M.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M].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90] COLLIER S J, ONG A. Global assemblage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M] // COLLIER S J, ONG A, eds. Global assemblages: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London: Blackwell, 2004.
作者:伊格纳西奥·法里亚斯,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志研究所都市人类学教授。ignacio.farias@hu-berlin.de
译者:杨舢,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y_sampan@sina.cn
排版 | 顾春雪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期刊精粹 | 城市组装——去中心化的城市研究对象【2025.1期主题·优先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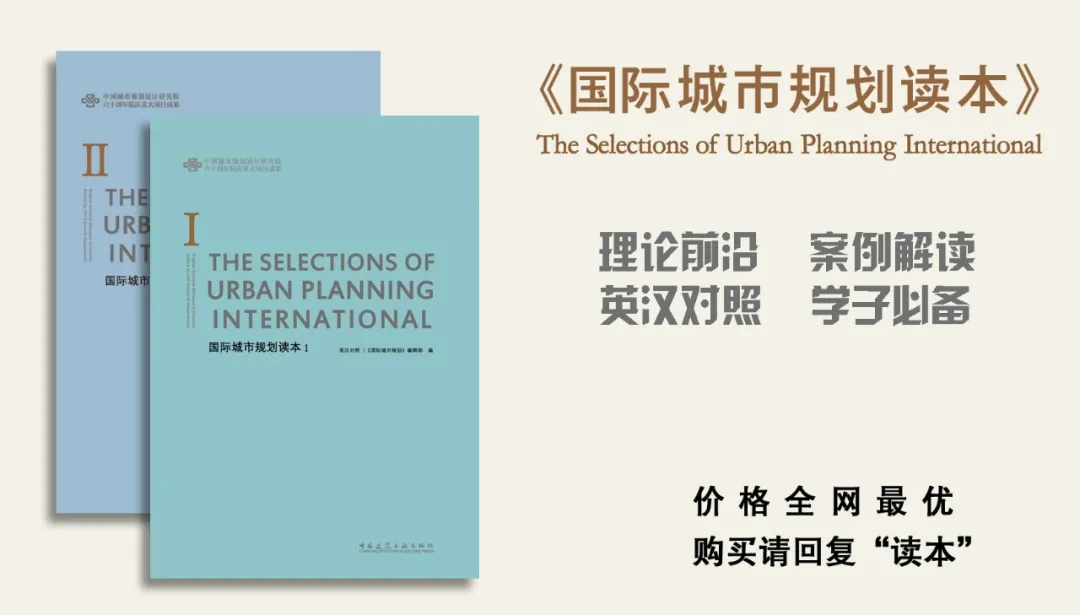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