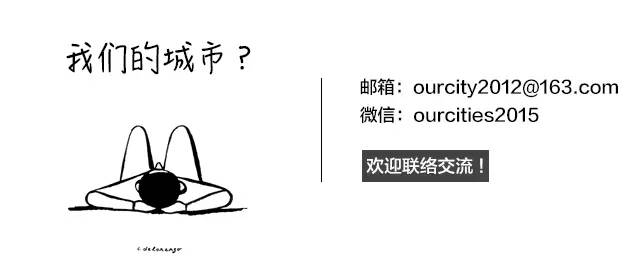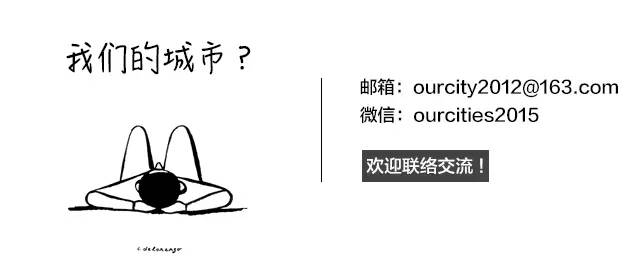你说,我们为什么选择离乡背井生活?每天挤着地铁上班、看着川流不息的景象,可曾有疲惫涌上?为什么故乡只能是精神信仰,而不能成为实实在在的生活之地?当我们将家乡与生活割裂,求的是否只是精神上的阿Q?

大伟兄弟在微信“朋友圈”一连发了几张照片,晒机票、晒行李、晒机场、晒自己。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从西安到昆明。事实上,这也是24岁,怀着一腔“创业”热血的年轻人第一次坐飞机。“飞机”这种交通工具,从1980年代末到整个1990年代,也同样带给Y先生以及我本人很大的冲击。我敢说,还从未有什么东西像“飞机”这样打破我们的时空观念。像是那首流行歌里唱的“明明早上人还在香港,还在九龙茶馆喝褒汤。怎么场景一下跳西安,我在护城河的堤岸……”当迁徙变得如此便捷而迅速,空间的巨大差异很容易带来不真实感,而在度过最初的冲击之后,随着“新鲜感”的失去,更多的则是对差异的麻木和视而不见。
看到大伟照片的时候,我人还在台北,准备在台社学会年会上发表一篇关于“返乡青年”的论文之外,顺便观光。于是也免不了将自己旅途的见闻以图片和碎片式的文字发到网络上,以示分享。这种行为在我的伴侣Y先生那里,是很不足取的,他总以为即时的网络分享只能证明我十足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大陆妹。对于这一评价,我以为还是有很必要反思一下,于是便发现了一个关于自我意识的秘密——在整个“福尔摩沙”的旅程中,我竟然很介意要将自己与“一般的观光客”区分开来。按照Y先生们的逻辑,这种区分只不过是更高一层“陌生体验”的表达,更加说明我作为一个土妞在面对“新世界”时的新奇感,毋宁说震撼感。有趣的是,大伟、我、Y先生恰似构筑了一幅金字塔的图景,大伟的网络留言是“好羡慕姐姐你能去台湾呢!那里一定比大陆好很多吧!”Y先生则在每天一通的电话中戏谑“你瞅人家贫民区也比咱这儿高端大气上档次吧?!”
当“金字塔”的层级结构成为社会形态与个人需求的唯一表述时,我大概无法否认Y先生的质疑。然而这种表述总令人生出一丝疑惑,甚或隐隐的不安,就像那些关于艋舺、龙山寺、大稻埕的简短的旅行感触,当我用iTaiwan的网络信号实时上传台北给我的直观感受时,观察的视角与感官的潜意识或许来自另一种资源,我称之为“乡土经验”。这种经验伴随着一个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你的故乡是哪里?”不止我,1980年代之后的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恐怕都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割裂感。像我这样,从出生便在“他乡”;成长中又随家人迁徙到不同地方;成年后也像同时代其他年轻人一样,去往超级大都市,在“更发达”、“更时尚”、“更国际化”的城市度过自己的读书生涯;间或有一些海外游历的短暂经历——无论怎么看,都像是攀爬金字塔的过程,稍不留神,还会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然而硬要我说出自己的祖籍,并使之等同为“故乡”,或许也充满无法言说的疏离感,而这恐怕要从我祖父辈的离乡进城说起。
我的父亲母亲在他们出生时就已经“进化”为城里人了,我母亲这一身份起始于外祖父的戎马生涯,1940年代外祖追随革命政权由陕北农村到了延安。尽管母亲对自己父亲当年的赫赫战功语焉不详,但他们兄妹五人的“红二代”身份,是确凿无疑的。而这在后来的“文革”中不仅没给他们带来好前程,反而耽搁了大舅舅的求学,还有我母亲的工作。到了她十六七岁的时候,延安城是无论如何待不下去的,于是只好去周边的农村下乡。比起母亲这一系的家族史,我父亲这一支则显得更有“现代”派头。1950年代陕西关中农村的祖父考上了省城的卫生学校,毕业后响应支边号召,去了更偏远的乌鲁木齐,在中苏医院当了两年医生之后却又回到农村老家。于是不得不提祖母,尽管老人家越来越喜欢提起当年事,我仍需依靠想象,来补齐在遥远的北疆那个“根红苗正”的关中农家小伙儿跟“发配边疆”的苏州城市商业主家二小姐的相识细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祖父辞去了公职,带着祖母回到农村老家,时隔一年,又为了带住惯城市的祖母离开农村,考取了西北农学院。我祖父祖母的故事在那个年代或许并不寻常,而且令人着迷,以至于我每每带着微笑跟朋友讲起,无一例外会收获他们或真心或夸张的赞叹“原来你有四分之一的江南血统!”
微笑的缘由并非因这“赞叹”而自得,更确切地说,恰恰是意识到这一句正是我的祖父母在六十到八十年代的三十年中聚散迁徙的根源。从我父亲出生到祖母最终落户西安,在我不完整的记忆中,一直伴随着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后来我才知道,当年祖父也曾经远赴苏州,为了一心念着“家乡”的祖母,想要在那里安顿下来,而我讲述的重点,就在这里。为爱辞职、考学、背井离乡的祖父最终没能成就浪漫骑士的形象,他在姑苏城生活了半年之后便落荒而逃,湿润的气候、精致的餐点和祖母心心念念的繁华富庶的江南生活抵不过关中农村的晴朗干燥、油泼辣子、椽头蒸馍以及乡音乡情的召唤,于是他们一个回到陕西,一个则留在苏州。我自己的故事就是从这里讲起的。
算起来,我的祖籍正是在关中平原东北部、渭河南岸的蒲城县,然而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童年时代唯一的一次“返乡”,父辈给曾祖父修坟立碑之后,再无瓜葛。尽管有七年时间我都随着父母在蒲城县所属的地级市生活成长,关于“老家”的记忆却少得可怜。然而回到1982年的那个秋天,陕甘交界的子午岭中,槐树庄农场的幼年经历让我以干部子女的身份,度过了最接近“乡土”的三年。在那之前,我的母亲抓住了难得的“招干”机会,将自己从农村分离出来,却不得不走到了离延安的家更远的地方。多年后,三岁小儿的“无意识”仿佛露出海面的冰山,农场的集体生活、熟人社会以及再也无法触及的最原始的自然,成为了我后来诸多抉择的更为隐秘的原因。时至今日,我偶尔会恍惚,觉得“槐树庄”其实根本就是我臆想出来的“桃花源”或者“乌托邦”,因为很快我就被“城市之光”震慑了。1986年在槐树庄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之后,我们举家迁移。大约是在我出生前,祖父就已经调动工作到省城。按照父亲后来的说法,因为没办法夫妻一同调动到西安,所以只好“曲线救国”。搬家的卡车在铜川歇了一宿,现在我甚至记不清在哪里跟父母分道扬镳了,但却清晰地记得我们驶入夜色中的铜川市中心,宽大的马路两边一排一排的路灯让我睁大了双眼,不断重复我有生以来学会的第一个音节“灯!灯!灯!”
后面的记忆全都模糊了,从“城市之光”一下子就跳到了西安,然后又跳到苏州,在那里我度过了学龄前的时光。所以我的确“有四分之一苏州血统”,但那却并不是一段美好的童年记忆。大概从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祖母的态度,那是一种连自家人都要分彼此的意识,这让我在想象祖父母的相识时,不自觉地补充了落难千金与农家小伙的情节,内心不免觉得祖母心底里是看不起农民,看不上北方的。可令人费解的是,在那个时代,无论从哪一面讲,祖母都不具备更大的优势,祖父在乌鲁木齐的“冲冠一怒”大约也是相当毁前途的。唯一的解释就只有爱情,我的祖父用他农民的浪漫,爱上一个城市千金,并试图爱上她的故乡。还好是在未经世事之前去到南方,否则我很难设想倘若经过现代教育,受过流行文化的召唤,我是否会留下童年创伤。这个北方小姑娘就在一群时刻强调南北差异、城乡差异的人中间,顽皮且快乐地成长,也学了一些规矩礼仪,甚至会说一口吴侬软语,却并不妨碍我想念遥远北方故乡的心情,像我祖父一样。
然而故乡在哪里?父母送走我之后,终于在距离西安很近的小城市渭南安顿下来,我在那里度过了小学时光。那几年过得颇为颠簸,先是随母亲借调西安,在那里借读两年小学,而后又回到渭南,在不同的地方读不同的年级——频繁的转学是大时代的缩影,如今当我看到随农民工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辗转于不同的学校甚至城市,便想起这段经历,只是我要幸运得多。1995年以前,我始终不认为渭南人和西安人有怎样的差异。就像我曾在一所农村小学读了一学期,从未觉得城市户口跟农村户口的孩子有什么差别,我们并没有多出一个鼻子两个眼,也不再用粮票、副食票划分生活层次,只一件事,我和大院儿里的小伙伴觉得有些得意,就是住家属楼。那么,房子在哪里,父母在哪里,家在哪里,哪里便是故乡吧。那套不足六十平米的单元房是我能追溯到的,最早的“故乡”,只不过,我们再一次扮演了匆匆过客。
终于搬家到西安。回溯我的童年及少年经历,竟然是一部父亲母亲奋斗史。他们带着我从陕北山沟沟里的农场到关中东部的小城市,再到省城西安,活脱脱走出了向上“进化”的道路。当我发现他们为了西安户口费尽心力,十年前的“城市之光”,此时不再是新奇的“启蒙”,而是若隐若现的压迫感。我没有像父母那样热爱西安,却也并不讨厌它,在西安读了两年小学的经历,使我很快融入到新的初中班级。小学同学的重聚掩盖了我是从外地转学过来的事实,如果一定要剖析一段“黑暗心灵史”,或许1995年3月的某个午后,我提着书包站在教室前面作自我介绍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脸红了。按照Y先生的逻辑,这很可能是出于自卑,顺便也就将考试第一名的经历解读为“乡下人”的自我证明。我不置可否。当这个世界只有这一种逻辑的时候,或许也就不会有后来“我的奋斗”。
十八岁,我去北京读大学,空间上离家越远,心理上却更贴近西安。成年后,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最初那个问题的答案,在“他者”的眼光中,无论是从历史文化的层面被“认同”还是在经济发展的角度被“排斥”,西安都成为帝都北京、魔都上海之外的,不可忽视的存在。我猜如果我的父母在以上这两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哪怕仅仅是周边地区,我或许会对这两座超级大都市充满热情;或者爱上某个执意要在那里生活的人,我也会甘愿做一个“北漂”;再或者换一个角度,当我以自己的能力在这都市中打拼出一片天地,并且将家人都安置在偌大的都市中,是不是就能理所当然地让自己走到城市的“金字塔尖”?这还不够,Y先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教育我“你还没冲出亚洲、征服美帝,怎么就能表现出这样肤浅的自我满足?”尽管“孝顺”与“顾家”是我与Y先生选择彼此作为婚姻伴侣的重要原因,对于“家”的界定,我却倾向于将其扩大为熟人社会甚或某种生活方式,就像我祖父当年所想念的故乡,于是便有了我对西安的认同。
看起来我是想用“乡土中国”的框架来抵抗“都市化”的潮流,或者是像Y先生描述的那种吃腻了肉蛋奶想吃大白菜的“逆都市化”的状态。然而回到家族史的叙述,我的祖母终于在1990年代之后迁户西安,住在祖父分到的第一套单元房中,过上更体面的生活,在各大名胜古迹为南方亲戚导游的时候,竟然多少也表露出一丝满足感。至于现在,更是操着一口苏州口音的陕西关中话,给祖父下面条、拌疙瘩汤、做油泼辣子,也享受起全家团聚的天伦之乐。作为我们家最早“现代化/城市化”的祖母,多年后终于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层面认同了这座西北城市。而我的“故乡”,也正是这双重意义上的。
台湾之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醒地认识到西安之于我的意义。就像“一府二鹿三艋钾”里面的历史感、龙山寺与在地信仰的结合以及大稻埕的生活场域,它们无一不勾起我对西安的记忆。父母家住玄武路,毗邻“大明宫”,祖父住在习武园,紧挨“广仁寺”,而我则在秦岭北麓“悠然见南山”,太多的历史遗迹存留在生活场景中,似乎历史上的长安城替代了今天的西安,成为人们认同的对象。历史当然很重要,但倘若不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估计生产出的情愫与“帝都情节”别无二致。所以,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就像今天我们在任何一座现代都市中间看到的场景,如若不是行色匆匆、夹着公文包的公司员工,恐怕就是缓步移动、挂着相机的观光客,西安的不同正在于整个城市的节奏都像是观光客停停走走、悠然自得的步伐,人们似乎不大看重“效率”,闲散的生活态度颇似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到的“消遣经济”。
也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意义上,之所以觉得自己“并非一般观光客”,是因为我相信在当地朋友的陪伴下,看到了台湾不同的生活场景:台北101及世贸中心、四四南村、永和社区大学、艋岬、大稻埕、宝藏岩、万华、集集小镇、清水村乐龄中心、基隆港废弃的船坞……很感谢朋友们带我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台湾,这些经历让我关于“故乡”的表述也更为清晰:“故乡”所包含的除了空间地景层面,更有心灵与精神层面的双重意义。身处这个时代,我们很有可能轻易就失掉了前一个意义上的“故乡”,就像我的祖父辈与父辈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不可逆的离乡,我这一代则因为一开始就在“漂泊”,而从未归过“故乡”,我们是否就失去了讨论“返乡”的资格?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台社学会“重返民间”的年会上,同样来自大陆的学者质疑我们这些以“知识青年”为“漂泊主体”的人是否可以“代表”更广大的农民工,对他们来说,“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是更为现实的问题,或者,人们更关心的是大都市的身份认同与物质生活的关系。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它指向自我反思,就像在埔里的酒厂看到那句再熟悉不过的“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我的祖母终于认同西安,很可能是因为这里终于能给她更为安稳的城市生活;而我本人去帝都、魔都绕了一大圈,又回到西安,则很可能被解读成京沪两地博士学位者多如牛毛,为了不致沦落到教中小学的地步,不如回到二线城市教大学;至于西安,近十年“文化搭台、地产唱戏”的发展,使得历史被征用为可以卖钱的资本——在资本的逻辑之下,一切都是“多少钱?”的问题。按照这个框架,我们的panel discussion在会议上提出的“漂泊感”与“返乡”的命题就显得十分矫情,甚至很有些小布尔乔亚的调调。于是我不再执意于“对抗”主流的资本逻辑,不再追求“槐树庄”那田园诗般的“乡土经验”。如果可能的话,我更倾向于在那个隐形的却又无比强大的金字塔结构上开个天窗,看到另外的可能,无论是多样态的城市空间,不同的城镇化道路,还是建立身份认同的“另类”资源。
三个月过去,大伟外派工作似乎无限期延长了,他每天频繁在网络上更新自己的状态,有对新环境的不适,譬如当月便上吐下泻水土不服,也有充满愿景的事业规划,更多的则是对昆明这座城市的感触。他像飞机刚落地那天一样,仍保持着最初的新鲜感,走遍城市的大街小巷,去博物馆看城市的历史,看小饭馆门口的招聘广告,研究服务人员的薪酬——无一不与他的西安经验形成对照。Y先生猜测这孩子在昆明谈了恋爱,以至“乐不思秦”。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拒绝文艺地“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却无法拒绝因为一种生活而留在某个地方,当我们的家族史、个人生活史与某个地方建立起无法割裂的联系时,我们就找到了“返乡”的路。就像我那些留在北京或安定或漂着的大学同学,他们未尝不曾以故乡经验照见北京的繁华与空虚,然而每个都有自己关于这座城市的情感表述,尽管他们没有回到真正意义上的家乡,却或许以另一种形式建立起“北京认同”,从此他乡是故乡。至于我,可以有一百条认同西安的理由,最为重要的是,我生活在长安,而我的生活小富即安、食甘寝安、随遇而安、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