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墙·院 ——广州泮塘五约“微改造”三辩
冯江 蒲泽轩 汪田





图 5 泮塘五约微改造片区总平面 ( 深灰色为公产房 )



图 7 改造前后的直街 11 号山墙与五约外街









微改造前,除公房外,泮塘五约的建筑半数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半数由村内原住民居住。一期微改造工程于2019年6月完工,至年底已有近六成公房出租,活化后的商业空间集中于五约外街两侧的改造空间内。经过半年多的经营,商家对这些空间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二次“微改造”。三巷13号弧形展廊南侧和北侧、直街11号后座、外街9号临街处,在商家进驻后均用竹篱将原本可以用来“走街串巷”的通道封闭了起来(图15)。与之相似,“抽疏”后为居民和游客提供的公共空间也部分成为了杂物堆积、单车停放的场地,原本出于适应气候考虑“室内化”了的室外空间“公共”效果并不理想。

图 15 泮塘五约微改造后的公共空间现状
事实上,改造后的泮塘五约的公共空间在日常使用中出现了两种分化。一方面,原住居民日常休闲和集体活动均聚集在五约直街西端的三官庙广 场;另一方面,五约直街东段的改造片区则更多地商业化为游客活动场所。居民与商家呈现出“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绅士化”后的公共空间有意无意地将原住居民排除在外。
上述现象反映出了不同的“公共”空间内涵。微改造期望实现的是一种 类似公园般对于居民、商家、游客都具有同等“共享”权益的普遍意义上的 “公用”空间,居民则习惯性地凝聚在历史以来村落社群集体的“共用”空间,入驻商家后的改造空间则由于营业时间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租期内的“私人”空间。在人类历史上的农业社会阶段中不存在作为现代概念的 “公共”一词,类似事务属于“共同的”或“共有的”。“共用” 空间相对于“公用”空间,多了一层契约精神,在泮塘五约,就是村落各宗族之间共守的乡约。商家作为“微改造”后被置入村落这一传统社区中的一类人群,没有也难以在短时间内与居民发展出传统的“共用”关系,微改造后泮塘五约产生了“公用”空间和“共用”空间的相对分离。
由于村落的“共用”空间延续了居民的空间认知传统,虽然五约的大部分村民已经搬到了五约北侧的集体住宅,维系村落关系的日常节庆活动仍旧 会固定在三观庙前广场举行。泮塘五约在 2017年4月开始的二期微改造设 计过程中引入社区参与方法,听取居民对于社区微改造的意见和愿望,并反 映到设计中,取得了一定的社区融合效果,成为目前公认广州微改造设计与 社区参与相结合的代表案例。在实际推进中,受限于微改造的制度,社区融 合的速度往往难以达到绩效考核的要求。二期项目主要进行多、快、省的立 面整饬,而居民真正牵挂的项目却难以落地。泮塘五约传统“共用”空间核 心的三官庙的麻石门匾和门套,在开展了参与式设计活动后仍无处安放(图16),泮塘五约第一大姓的祠堂李氏敦本堂也一直处于有待修缮状态之中。

图 16 参与式设计过程中将三官庙门足尺模型摆放在三官庙广场
从“共用”到“公用”,不只是旧城村落空间设计的操作,更呼唤城市 社区中社会治理的改善。“公共”空间不是“公”与“共”的简单连通,传 统社区与现代城市的生活融合才能实现公共空间的真正共享。
4 余论:约
“约”,即乡约,是多姓所共同制定和遵守的契约。乡约可刻字成碑, 置于以“乡约”为名的建筑之内,供乡人阅读,起到教化的作用。“约”实质上包含了三重意义,即乡约本身、放置乡约的空间和乡约所管理的社区。泮塘五约是李、黄、梁、刘等多姓共居的宗族村落,在泮塘五约西侧靠近荔湾湖的村口大榕树下,至今仍保存着仅剩“正立面”石门匾和石楹联的小亭 (图17),门匾上书“半溪”两个大字,正中竖刻“五约”两个小字,楹联为“门接水源朝北极,路迎金气盛西方”,为清代同治年间进士、泮塘五约人黄其表所提。门匾和楹联组成的石门套构件与红砖墙和辘筒瓦顶共同砌筑而成,地面为条形麻石铺砌,后墙用于张贴村内的通知和告示,发挥着“乡约”的作用。

图 17 半溪五约亭现状
“微改造”“微更新”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拆建模式的城市更新方式,强调改动之“微”与干涉之轻,是体现城市更新“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原则的重要方面。与制度性的探索相匹配,历史环境中的建筑微改造应寻找一种真正延续历史文化、尊重本地居民和原有形态特点的模式,让历史环境在各种诉求的互相理解和促进中“共生”,而不是退回到“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完善”的市政层面(以《广州城市历史城区微改造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 年 )》《广州市老旧小区 微改造三年(2018-2020) 行动计划》等文件为代表,广州近年来的“微改造建设标 准”中并不包括实质性的居住建筑空间环境改善的内容。恩宁路和泮塘五约的微改造成为了不可复制的典型案例),或者将其当成一种营利手段。
作为一种存量时代的城市发展模式,现阶段的微改造本质上仍在追逐土地的增值,通过旧貌改造提升城市形象带来社会效益、尤其是公共资产的增值,通过空间改造转变产业获得经济效益的增值,如此则城市不可避免地绅士化。在这个意义上,存量时代与增量时代的城市更新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在这一前提下,建筑学几乎难有作为,只能制造看起来更加“高级”但却内涵苍白的空间。
社区层面的微改造不涉及用地功能或规划指标重大调整(与之相对应的是,《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明确“城市更新”是“对低效存量建设 用地进行盘活利用的活动”),注重在微观层面构建社区内部的参与、协商机制,重视居民,尤其是原住居民的意愿表达,旨在培养和提升社区意识、社区认同、社区精神。社区微更新的本质是社区治理,是社区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推进社区发展的持续过程。事实上,这与历史上的“约”颇有相似之处,订立共同遵守的契约,在乡规民约的约束之下延续公序良俗,提供物质空间改善指引的同时,在合适的土壤上传承地方文化、增进社区融合、凝聚社区精神,方为社区微更新和建筑微改造的实质目标。
在巨大的利益、效益面前,个人的声音经常被后置乃至遗忘,正如因为拆迁问题而形成的“海珠之眼”(图18)(广州市环岛路海珠涌大桥通车后车道中间保留的“桥中房”),它虽然形似一只眼睛,却只能在屋主的无奈和决策者看似合理又包含了乐见其成意图的解释所编织而成的复杂情绪中被众人围观,无法看到自己的去向。(END)

图 18 海珠之眼

《空间演替》为2021年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课程建筑学科理论前沿综述·城市更新专题初次辑录
为2022年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第十五次研究会“地域空间史研究的门与墙”首更
撰文 冯江 + 合作者 编辑 郑安珩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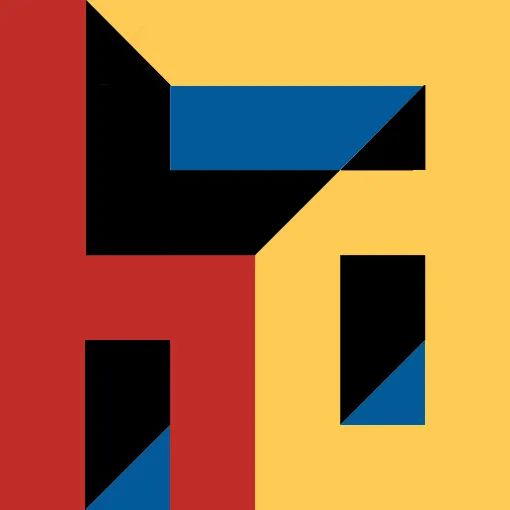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建筑遗产学刊):空间演替 | 门·墙·院 ——广州泮塘五约“微改造”三辩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