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20年8月开始,梁鹤年先生受《中国投资》杂志邀请开设专栏,将他对中国与国际种种问题的思考写成杂文,与读者交流探讨。本号则从今年4月20日开启了新专栏——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四位青年学者将在本系列连载中分享他们阅读这些文章的感悟。
希腊哲学重秩序,具有万物本源是“数”的求真思想,体现在人居环境上是其几何化、秩序化的第二自然的呈现,然而,“私利可达公益”为资本逐利戴上了普世价值光环后,城市建设便从“为整体人民生活得更高贵”变成了盈利与否的估价开发。
资本主义文明确有很多令人羡慕的成就,但目前看来,资本逐利、利益至上的思维逻辑,几乎使人们丧失了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持续发展的真实面目也清晰暴露出来。我国近现代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借鉴,然而今时今日,应当谨慎吸纳西方的长处为我所用,不数典忘祖,不简单照搬。
不数典忘祖,是不忘中华文明之根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五千年兼容并蓄,“旱九年而不枯,受八州水而不满”,文化根基稳固。这是伟大文明必备的气质,但不是中国人生而就能拥有的能力,在学习吸收的同时仍需记得“来时的路”。“善学邯郸,莫失故步”,值得警惕。
不简单照搬,是要找到“他山之石”的正确用法。别人的经验有时并不直接可用,系统、条理地分析他们的做法(手段)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才对我们在特定环境中采取行动具有实际启发和借鉴意义,因为手段与背景元素的匹配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什么是背景?成功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是解决问题和追求目的时的约束和条件,是必须考虑的背景元素。什么是手段?手段是你的“手”可以掌握的才算,即当下你掌握的人力、财力、知识和组织资源允许你干的事情。因此,特定思维逻辑指导下形成的符合特定人、事、时、空的方法才能解决特定问题。例如:若要基于甲地的经验,为乙地创造出适宜的手段,真正的挑战在于观察分析好甲地手段与背景之间的匹配情况后,立足乙地背景,为乙地创造出能够与之匹配的手段[1]。这是因为甲地背景与乙地背景都是独特的,且不易改变;甲地的手段是现成的,也不易改变[1]。这也是我们在借鉴学习国外经验时,不忘中华文明之根本的原因所在,即要找到属于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特定背景。
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写道,“创造表面上和一阵风一样变化莫测,实则也像风一样有许多确切的条件和固定的规律。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2]。这也印证了特定的背景与特定的手段之间有着怎样密切而又强大的关系。
“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体系,发挥借鉴内化的传统优势,固本培元,守正创新,避开“资本为王”的泥淖,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正确道路。
[1] 梁鹤年. 论方法(3):比较[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0(ZA): 26-28.
[2] 丹纳. 艺术哲学[M]. 傅雷,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作者:于东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基于比较的主动求变
《中国投资(中英文)》于2020年11月刊载的梁鹤年先生的《论方法(3):比较》一文中谈道,人易受时代影响,或稳中思变或变中求稳;凡变都有代价,变越大代价越高;不是凡变必好,更不能“为变而变”,既要看变的代价,更要看变出来的东西比现在的东西好多少,支持“要变才变”[1]。我认识到,变的承载主体可以是万物,而以人为推力的主动求变,究其根本,是源于比较后的一种选择。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通过思想整理观察到的外在事物信息并赋之规律(秩序)后,我们可以明白(understand)。所谓明白,就是我们的思想整合了内在的理念和外在的观察[2],这是规律与认识从比较到匹配的过程。在实践中,我们在比较后往往会选择改变、运用和实施,但比较非简易之事:从品牌企业生产,到地区发展,乃至国家之间的相互借鉴,从物质商品、机器设备的硬件,到政策法规、组织系统的软件,纳入比较的内容和比较的过程都需要慎之又慎,需为求善向上打下的坚实基础,积“万里之跬步”。
基于比较之上的主动求变是聚焦于某一目标的具体行动,不同于独树一帜、光怪陆离和离经背道等异于常理的“变”。普世性情况下的“变”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通过观察分析找到一些相关规律的蛛丝马迹。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将应变或求变的法则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即“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这也是梁鹤年先生的“背景迁移分析”(shift of context analysis)比较研究法的精髓。该研究分析法采用4个变量(甲地手段、甲地背景、乙地手段、乙地背景)、2个关系(甲地手段与甲地背景的匹配、乙地手段与乙地背景的匹配)和7个步骤,分析创造出一个能够与乙地背景匹配的有效手段[1]。整个过程为比较后求变提供了系统化的、踪迹可寻的依据:首先,第1~3步明确甲地的手段(事)和鉴别甲地的背景元素天时、地利、人和(时、空、人),分析手段和背景的匹配情况,为后续步骤铺路;其次,开展脑中“臆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即第4步,假设把甲地手段原封不动地套在乙地上,这个过渡性场景的设置对之后的选择至关重要,为“变”的方式提供了有理有据的“灵感”;最后,第5~7步通过考虑甲地手段与乙地背景可能的匹配度研究,或原封不动、或稍作调整、又或另起炉灶地借鉴甲地手段。整个过程反映出对待变前的慎重态度和追求变后的足够效率,但同时强调,即使是目的性极强的求变,我们也应追求与背景非常匹配(天时、地利、人和,时、空、人)的手段,虽然它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手段(解决问题、达成目的),但会是一个最稳定的手段。要特别注意,眼下最有效的手段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眼前较好但最有潜力的手段也许才是最妙的选择。
为何主动求变要慎之又慎?《周易·系辞上》有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通其变,使民不倦”“变通者,趣识者也”。可见,只有掌握求变的规律,才能应时顺势,摆脱困境,顺畅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反之,则可能阻力重重,使整个局势深陷徘徊、停滞甚至后退的状态。如何应变?亚里斯多德认为“变”由“因果同类”启动,是从“潜质到实现”的过程[3],这说明了应对变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则,是要针对现存的问题,用现有的能力去解决。就城市规划者而言,在社会期待我们创造美好空间的背景下,应充分考虑空间变化因果的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因素(即时、空、人变量),聚焦于对处理城市空间(事)职能的主动应变。
[1] 梁鹤年. 论方法(3):比较[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0(ZA): 26-28.
[2]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521.
[3]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45-70.
作者:王冬银,博士,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统筹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特色——“是何”到“为何”的思考方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是一般规律和本国特色的融合,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本国国情的鲜明特色[1]。报告同时提出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1]。这些定义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何。可以看到,中国特色是以与其他国家比较为基础,通过区分规律与特点做出的阐释。这种比较是研究特色的典型视角,即通过案例比较获得经验,并因地制宜地修正这些经验,从而更好地借鉴。
每个案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对其加以修正,这是常识。然而,这些经修正的经验在实施中有成有败。需要探讨的是,到底是因为修正而成功(或失败),还是原经验尽管被修正也还是成功(或失败)?认识这种修正真正的作用即为何成功(或失败)的过程,有助于识别哪些是有效的经验借鉴以及哪些是有效的修正,而这需要针对比较进行系统化的分析。
本文是梁先生“方法论三部曲”的第三部,阐释比较的方法,特点在于用一套清晰的逻辑与流程去分析不同背景下如何实现借鉴。这套方法被称为“背景迁移法”,强调“背景—手段”的关系,正如文中形容的,“要看看人家的东西(手段)在人家的土壤里(背景)是如何生长和发挥作用的,然后去芜存菁,移花接木,洋为中用”[2]。
“背景迁移法”大致包含7个分析步骤[2]:
(1)甲地“手段”;
(2)甲地“背景”,即分析“手段”实施涉及哪些关键背景元素;
(3)甲地“背景—手段”的匹配关系,即是否出现吻合、矛盾、张力关系;
(4)甲地“手段”迁移到乙地“背景”,即是否类似步骤(2)中,乙地也存在关键背景元素;
(5)“甲地手段”与“乙地背景”的匹配关系,即是否类似步骤(3)中出现吻合、矛盾、张力关系;
(6)基于“乙地背景”分析“甲地手段”的可塑性或因地制宜地被修正的极限;
(7)基于步骤(5)与步骤(6)识别与“乙地背景”适应性最强的手段,即与乙地关键背景元素最吻合、矛盾最少、张力最小的手段。
笔者认为,这套背景迁移法不仅有方法层面的价值,更有认知层面的重要价值。正如前文所论述的,目前“现代化≠西方化”已形成基本共识,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也得以明确。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基于这五个方面的特点为何以及如何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手段”去应对相关问题?
比如:从特点一“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出发,其余四个特点都涉及“平衡”的手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包含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财富平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发展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包含了满足不同代际发展需求的资源配置平衡;“走和平发展道路”包含了国际关系中本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
这些需要平衡的问题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存在类似问题并已有很多平衡“手段”的探索。从背景迁移法的视角看,基于西方手段获得启发,并形成中国特色的手段,至少有三种路径:(1)针对与西方背景吻合或成功的手段,创造出该手段迁移到中国背景的适用条件;(2)针对与西方背景矛盾或失败的手段,识别该手段迁移到中国背景的应用潜力;(3)针对与西方背景有张力的手段,创造出该手段迁移到中国背景的改良方式。
这些启发和创新与聚焦“成功”经验的比较方法相比,强调的是“背景—手段”关系,即从成功、失败、有张力的适配关系中去寻找启发与实现创新。这不仅有助于拓宽可借鉴手段的范畴,也有助于理解这些手段的应用条件、适用逻辑和预期效果,还有助于实现从识别“中西差异”到建立“中国特色”。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2023-08-07].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10/25/c_1129079926.htm.
[2] 梁鹤年. 论方法(3):比较[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0(ZA): 26-28.
作者:李媛,博士,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治理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系列文章
01 解读《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梁言实录 | 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连载】(6)解读《论方法(3):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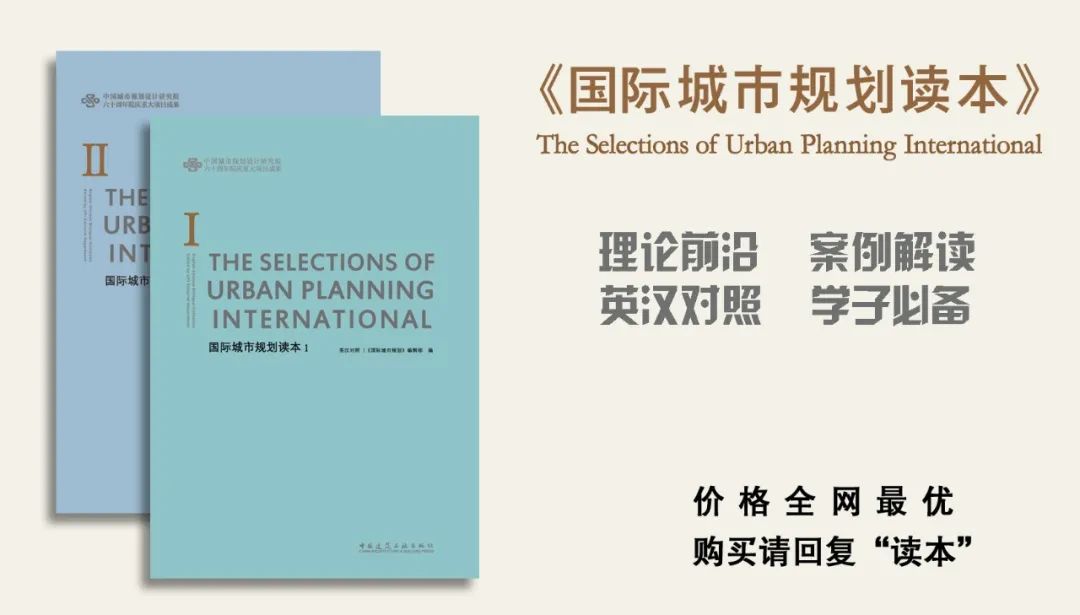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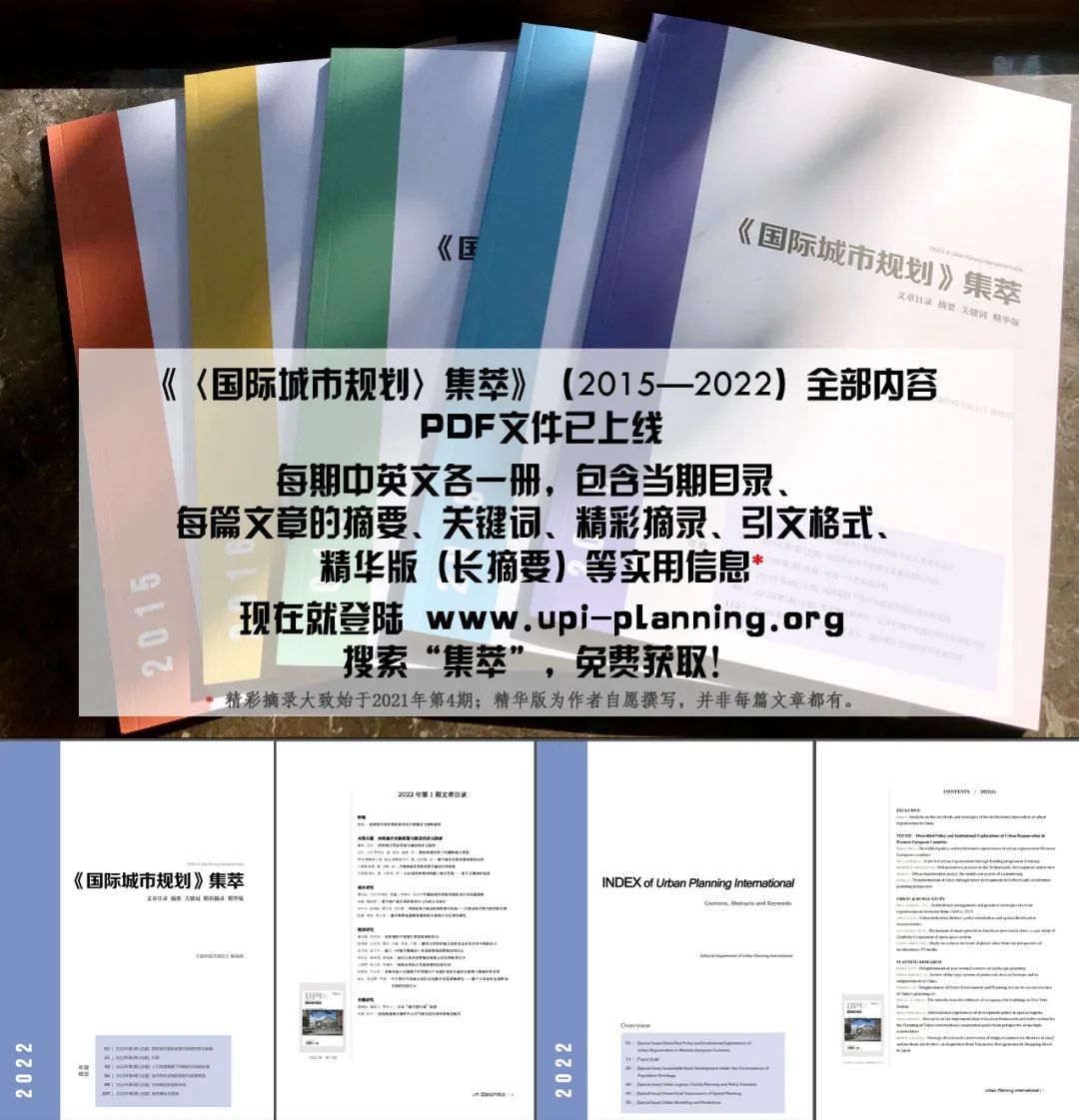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