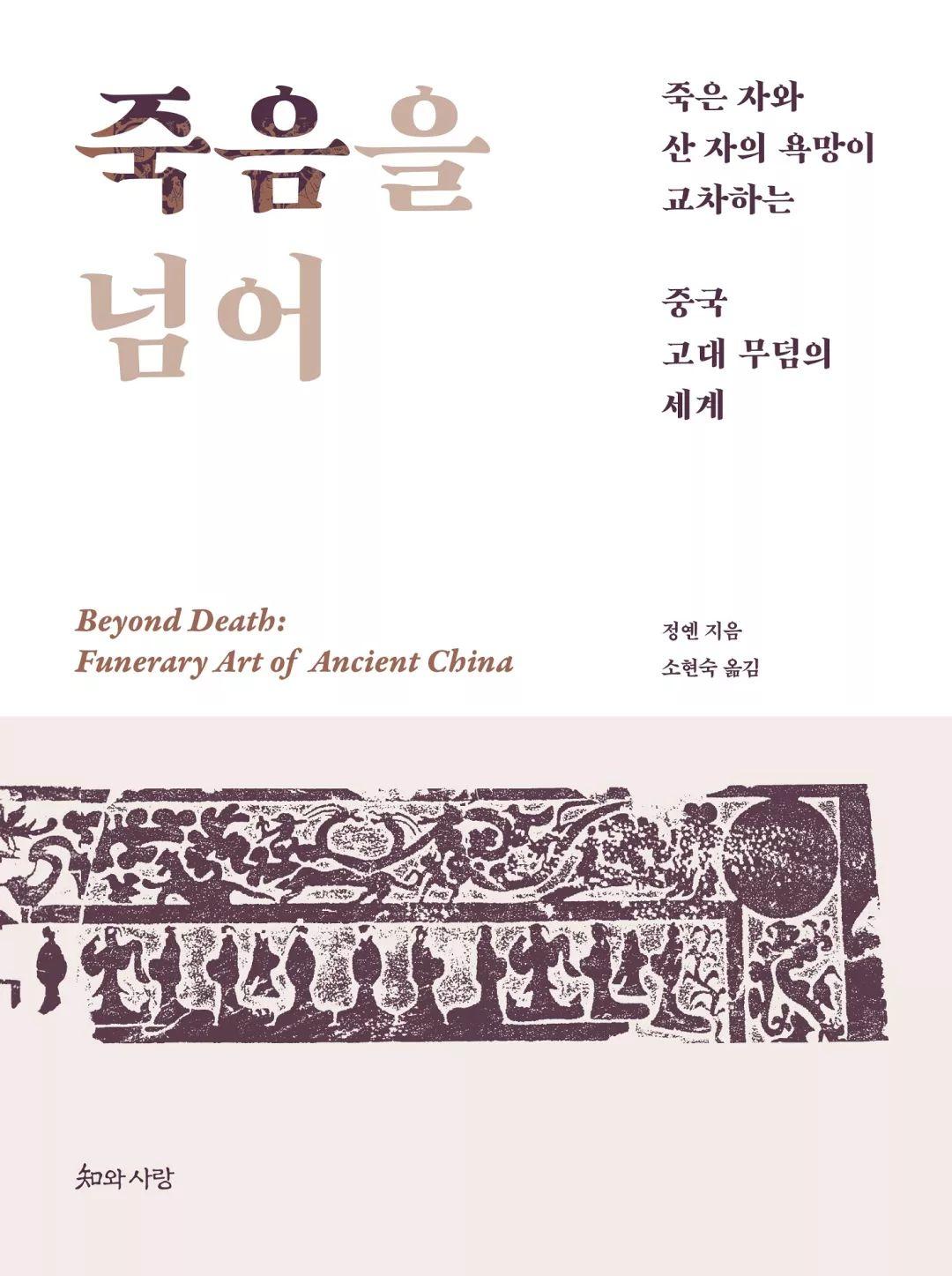
作 者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美术考古研究。主要专著有《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郑岩自选集》《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美术研究》《看见美好:文物与人物》《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合著《山东佛教史迹:神通寺、龙虎塔与小龙虎塔》《庵上枋:口述、文字与图像》等。
致韩文读者
在古代中国,一些偶然发现的古墓葬对于学术研究曾产生过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安釐王(另一个说法为魏襄王)墓中盗出数十部竹书,便是古代典籍的一次重要发现 01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中,记载了许多古墓和祠堂,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神秘的古代陵墓还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成为许多文学作品的背景 02 。从北宋以后,金石学家对墓志碑版,以及墓葬、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进行深入研究,成果丰硕。但是,总体上看,这类工作过于零散,由于对死亡的禁忌,墓葬并未成为传统中国学术研究自觉而明确的对象 03 。金石学家虽对于墓中出土的古物用力甚多,但却不注意墓葬本身的研究。直至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近代田野考古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已从专门针对艺术品和文字材料的“挖宝”阶段,发展到了平等地看待各种材质的遗物、系统提取各种信息的时期。1928年到1935年中央研究院对于河南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目的已不局限于寻找甲骨文和艺术品。在殷墟发现的多座商代大墓虽在历史上已屡次被盗,但考古工作者还是通过科学的发掘,获取了完整的墓地布局、墓葬形制等信息,为研究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1958至1959年考古学家对于陕西华阴县横阵遗址仰韶文化埋葬坑的发掘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该墓地发现的3座“大坑套小坑”的二次合葬遗迹,成为研究史前丧葬习俗和家族制度的重要依据 04 。
基于系统的考古学材料,传统的器物学研究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例如郭宝钧1981年出版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 05 ,提出了“界标法”,即从铜器的“群”和“组”的角度出发,联系到出土铜器的墓葬,确定了商周青铜器分期的六个界标,再从铸造、器形、花纹、铭文四个方面将中国青铜文化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又着眼于礼乐器群的组合,进一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这种方法的前提是,田野考古工作中已经获得了数批墓葬和窖藏出土的成组合的青铜器。这比起依据博物馆和个人收藏的零散器物进行类型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学界还对古代墓葬制度本身进行了系统、宏观的观察 06 。
中国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美术史是获益巨大的学科之一。在日益丰富的考古材料支持下,中国美术史写作的广度与深入不断增加。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学与美术史学两个学科密切接触。概括地说,主导这两个学科之间相互联系的有两个基本框架,一是对于“美术”这一概念的理解,二是中国的“画学”传统。
起源于欧洲的“美术”(fine arts)一词的演变历史相当复杂 07 。1568年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年)在第二版《大艺术家传》(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ori)中,将绘画、雕塑和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认为它们皆来源于design 08 。与design一词对应,17世纪的法国出现了beaux-arts一词,不仅包括绘画、雕塑和建筑,也涵盖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形式。至19世纪,这个法文词的地位逐步为英文的fine arts(或第一个字母大写的Art)所取代而影响整个欧美,其意义则局限于“高级的”而非实用的视觉艺术。与之相应,线性的西方美术史写作也建立在这种历史形成的“美术”概念之上。在反对艺术纯粹化、贵族化的道路上,1918年以后,德国率先将美术学院与工艺及设计学校融为一体,确立了20世纪美术学院的基本格局 09 。20世纪初,美术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并沿用日文的翻译。中国早期新式的美术院校系科划分,也基本上遵循西方和日本的方式。由于较早的中国美术通史教材同样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并且将其读者设定为美术院校的学生,这就使得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框架基本上延续了西方的传统分类。1957年,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建立在中央美术学院,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倾向,使得原本在西方作为一门较为独立的人文学科存在的美术史学,更像一种专门史。
依靠传世的作品,显然难以满足近代美术史书写的结构,而考古学材料正好及时地提供了新的资源。其中,除了地上保存完好的石窟和古建筑,最重要的材料来源于古代墓葬与遗址。墓葬是人类基于信仰和希望而进行的有意识的埋藏,一般说来,比城市、村落等聚落遗址保存得更为完好。墓葬中出土的葬具、随葬品、壁画,包括墓葬建筑本身,在“美术”的框架中被按照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建筑加以分类,墓志、墓碑、简帛等则成为书法史研究的对象。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便是按照“绘画编”、“雕塑编”、“工艺美术编”和“建筑编”进行分类,墓葬中发现的壁画、画像石、俑、青铜器、瓷器、金银器,以及陵园、祠堂和墓室,分别划归到这些门类中。
以西方美术的概念看待中国艺术的历史时,最容易与之对接的是中国固有的“画学”。中国历史悠久的卷轴画便于携带、移动,形态与西方架上绘画类似。中国绘画至迟自六朝时期就已被有意识地收藏、记录、临摹、品评。比起雕塑史、建筑史和工艺美术史的书写而言,中国绘画史写作的基础和资源更为深厚。但是,由于中国绘画所使用的绢帛纸张质地脆弱,早期绘画的实物难以流传,传世者多是宋代以后的作品,唐代绘画实物已是凤毛麟角,更不必说年代更早的作品。而在这一点上,古代墓葬出土的壁画、帛画和其他形式的绘画,以及石窟中的壁画自然成为重要的补充。在以墓葬遗存为主的考古学材料的支持下,中国绘画史的写作在时间范围上甚至延伸到新石器时代。
就美术史的写作而言,用一种由西方引入的关于“美术”的传统分类来看待墓葬材料,固然有可能建立起诸如雕塑史、建筑史等与西方“抗衡”或“平行”的专门史,但也限制了我们对于原始材料的理解。同样,利用墓葬材料建立的绘画通史固然看上去更为完整,但也容易忽略墓葬材料本身的属性。在许多此类著作中,新鲜的考古材料只是根据西方传统的“美术”门类的划分方式或后世绘画的概念,被加以选择和解释。在这个过程中,遗物之间内在的联系、遗址和墓葬整体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实际上与使用博物馆藏品或传世品并无本质的区别。
以上两种倾向类似于考古学所说的“补史”、“证史”作用。这种说法将考古学设定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一个未能言明的前提是,在考古学之前已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史”的系统,考古材料的作用,在于使之更为完整。与之类似,美术史对于考古材料的使用也有其前提,即一成不变的“美术”概念,以及传承有序的绘画史。这种方式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并未立足于中国历史本身内在的逻辑来看待美术史,也未从考古材料本身提出新的问题,而是从另外的知识系统进入这些新的材料,从已知的结果回溯到未知的过去。
相对于上述倾向,“墓葬美术”概念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巫鸿2007年提出这个概念时,甚至设想将其视为中国美术史研究中一个“可能的”“亚学科” 10 。“墓葬美术”一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英文中的funerary art。然而,西方美术史研究虽然不乏对于墓葬美术的具体研究,却没有自觉地将“墓葬美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来看待。巫鸿本人在其英文著述中,除了使用funerary art,更多地使用tomb art一词,后者可能更准确地对应其中文的表述。实际上,这个概念源于巫鸿对于东汉武梁祠的研究。1989年,他在《武梁祠》一书中,强调祠堂建筑与画像内在的结构性关联,即画像的原境(context),从中寻找出解读图像意义的程序(pictorial program) 11 。整体性地解读墓葬材料的方法,与考古学对于墓葬的发掘和记录方式十分一致,而区别于古董收藏和博物馆的分类。
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年)认同这样一个说法:“从人类历史最古老的时代开始,葬礼美术就比其它艺术形式更为清晰、直接而明确地反映出人类的形而上学信念” 12 。法国当代文学家和哲学家德布雷(Régis Debray)甚至声称:“图像诞生于墓葬” 13 。在他看来,那些与死亡相关的早期图像包含着宗教的魔力,正是这种力量支持着图像不断发展。这些说法对于中国墓葬美术的历史同样适用,例如,通过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的帛画来讨论汉代的宗教思想,成为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普遍的做法,而这样的研究,也使得美术史本身大大突破了旧有的学科定位。巫鸿所强调的“原境”,并不只是墓葬图像的一种阅读顺序,在更高的层面上,这一角度还将墓葬看作与特定的人、地域、宗教、时代等元素密切关联的物质元素,例如,从这种方法出发,可以将墓葬理解为丧礼和葬礼的结果,反过来可以由此探索丧葬的礼仪与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风俗和思想背景。这样,由“死”返“生”,墓葬便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一个通道,在方法上也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合作与沟通。
上述研究角度的转换,也与艺术在当下意义的变化有着一定的关联。当代的艺术实践已不再局限于高贵、庄重、典雅、精巧的纯美术,传统的形式、媒材、语言的界限被打破。在新的艺术实践的启发下,重新审视古代更富于观念性、功能性的墓葬美术时,可以将一座墓葬视作一件整体性的艺术作品,甚至包括各种相关的仪式,都可以看作一种具有艺术特征的行为。在我看来,墓葬可以被理解为安置死者肉身的处所;可以被理解为建筑、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等艺术形式的集合体;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生死这个最大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下,以物质的材料、造型的手法、视觉的语言,结合着相关仪式所构建的诗化的“死后世界”(至少是其一部分)。在后一个层面上,它也可以被整体地理解为一种具有功能性和终极价值的艺术作品,而不只是一个放置死者肉身和“艺术品”(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作品)的盒子。
墓葬美术的概念,还有助于我们反思美术史研究中一些基本的方法。例如,与西方古典时代后期的嵌入墓(enfeus)和中世纪哥特式的墙墓(wall tomb)纪念碑式的展现方式不同,中国的墓葬主要以埋藏为特征,即《礼记·檀弓》所谓“葬也者,藏也”。因此,基于“观看”而发展出来的美术史形式风格分析的各种方法,就有必要进行重新的审核,进而探索中国墓葬美术内在的逻辑。我们还可以由此思考“彩陶—壁画—卷轴画”这类单一的故事线索所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最终也将促使我们从中国历史的角度重新思考对于“美术”的理解。这些工作目前虽然并未深入展开,但我们已经能够初步地意识到其潜在的理论意义。
当然,墓葬美术这个概念仍旧像是传统“艺术品”概念的升级版。这个概念形式上可以与卷轴画、石窟艺术、青铜器艺术……等并肩而立,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研究者的分工以及特定的训练,卷轴画、石窟艺术、青铜器艺术等,已经或多或少地成为一个个封闭的领域。墓葬美术概念的提出,如果说基于对于此类封闭性概念的不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它成为另外一个封闭的领域。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反思“墓葬美术”的概念,特别是要警惕它成为一个画地为牢的词语。这个词语的历史使命在于帮助我们打开思路,建立一个讨论的平台,而不是建立一个“学派”。
目前关于中国古代墓葬美术的研究还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许多环节还十分薄弱。例如,在中国考古学资料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美术史的研究却积累不多;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还没有有效地展开;方法、观念的更新与材料日新月异的增加无法匹配;当这类研究在跨越了美术史原有的界限时,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也需要随时补充完善……诸如此类的问题,远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甚至不是一代人和一个学科所能突破的。我在这里粗略地介绍我所了解的关于中国墓葬美术研究的情况,也希望得到韩国同仁们对这类研究工作的关心、支持与批评。
接下来,我对这本书做些简要的说明。
这本书中所收入的文章是我20年来研究中国古代墓葬的一些心得,所讨论的范围集中在两汉到南北朝时期,少部分涉及唐代乃至辽宋金元的材料。这些文章在书中按研究对象的年代依次排列,但这并不是我写作的顺序。20年来,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前后有一些变化,这除了与上述学术倾向的变化有关,也与我在此期间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变动有关。我曾在山东省博物馆服务多年,2003年到中央美术学院教书,由博物馆和考古学领域进入美术史研究的新天地。这些机缘使我有机会观察、理解和反思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于同一类材料的不同的研究方式。我认为,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之间,除了差别和对立,或许还可以寻找一种彼此补充、相互兼容的模式。因此,我试图通过一些尝试性研究,获得更多的途径,去发掘考古材料中所包含的丰富信息,从而探索建立这类关联的可能性。因此,我并不过多地强调学科纯粹性,也不去纠结问题和方法正宗与否,更不以形成固定的风格或模式为目的。我们需要进行更加多维多元的试验,而不是贸然作出结论。要做的工作太多,这本书只能反映我个人的阶段性认识。我期待各位韩文读者对我的指教。
这本书的基础是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逝者的面具:古代墓葬艺术研究》,删除原有的“前言”和两篇文章,又增加了五篇近年来的新作。我特别感谢译者苏铉淑博士的帮助。这本书的翻译,花费了她大量心血,我因为这些不成熟的文字浪费了她宝贵的时间而感到十分惶恐。我也要感谢金红男教授对我的鼓励并赐序,是她最早提议翻译这些文章。感谢杨泓先生多年来对于我的教导。感谢出版社的各位朋友。
郑岩
2017年5月26日于北京
注释:
01 关于中国古代盗墓的研究,见王子今:《中国盗墓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02 相关研究见张玉莲:《古小说中的墓葬叙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这类文学作品最新的例子是目前流行的《盗墓笔记》、《鬼吹灯》等中国网络小说。
03 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宋哲宗朝元祐年间(1086~1094年),赵仲忽进献“周文王鼎”,有人称此乃“墟墓之物”,应治其罪。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二,第五叶,泊如斋重修,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刊本,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藏。
0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39页。
05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06 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332~337页;王仲殊《中国古代墓葬概说》,《考古》1981年第5期,第449~458页。
07 中文语境中的有关讨论可参考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美术研究》,2003年第4期,第60~71页,2004年第1期,第14~23页;黄大德:《“美术”研究》,《美术研究》,2004年第2期,第4~11页;邢莉、常宁生:《美术概念的形成:论西方“艺术”概念的发展和演变》,《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5~115页。
08 范景中主编:《美术史的形状: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2~31页。
09 Nikolaus Pevsner, Academies of Art, Past and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0;此据中文版,见佩夫斯纳:《美术学院的历史》,陈平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203~241页。
10 巫鸿:《墓葬:可能的美术史亚学科》,《读书》2007年第1期,第60~67页。
11 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中文版见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12 Erwin Panofsky, 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此据中文版,见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86页。
13 Régis Debray, Vie et mort de l’image: Une histoire du regard en Occident, Paris; Gallimard, 1992;此据中文版,见雷吉斯·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黄迅余、黄建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目 录
中国墓葬美术的胎动(金红男)
致韩文读者
译者序(苏铉淑)
一 汉代
风格背后: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新探
关于墓葬壁画起源问题的思考:以河南永城柿园汉墓为中心
西汉石椁墓与墓葬美术的转型
山东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的形制及其他
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形象
关于汉代丧葬画像观者问题的思考
弯曲的柱子:陕北东汉画像石的一个细节
二 南北朝时期
葬礼与图像:以两汉北朝材料为中心
墓主画像研究
墓主画像的传承与转变:以北齐徐显秀墓为中心
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
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
北齐崔芬墓壁画初探
北朝葬具孝子图的形式与意义
三 唐至元代
压在“画框”上的笔尖:试论墓葬壁画与传统绘画史的关联
唐韩休墓壁画山水图刍议
夕阳西下:读兴县红峪村元代武庆夫妇墓壁画札记
论“半启门”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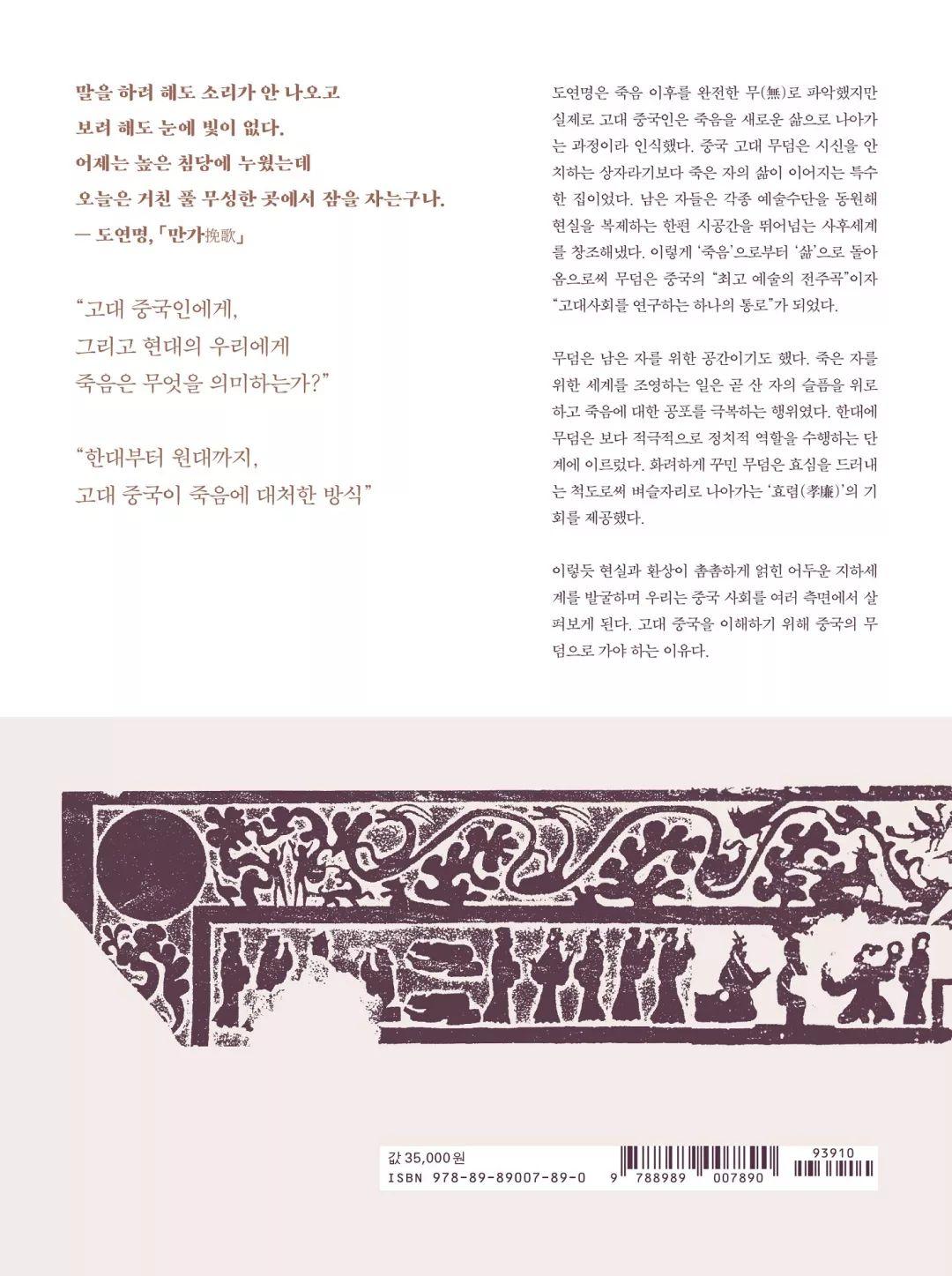
超越死亡:中国古代墓葬美术(韩文版)
郑岩 著 苏铉淑 译
韩国三星美术出版社
2019年12月
ISBN 9788989007890
定价 35,000韩元
相关链接:
美术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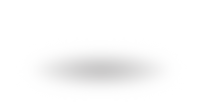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美术遗产):图书资讯丨超越死亡:中国古代墓葬美术(韩文版)
 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