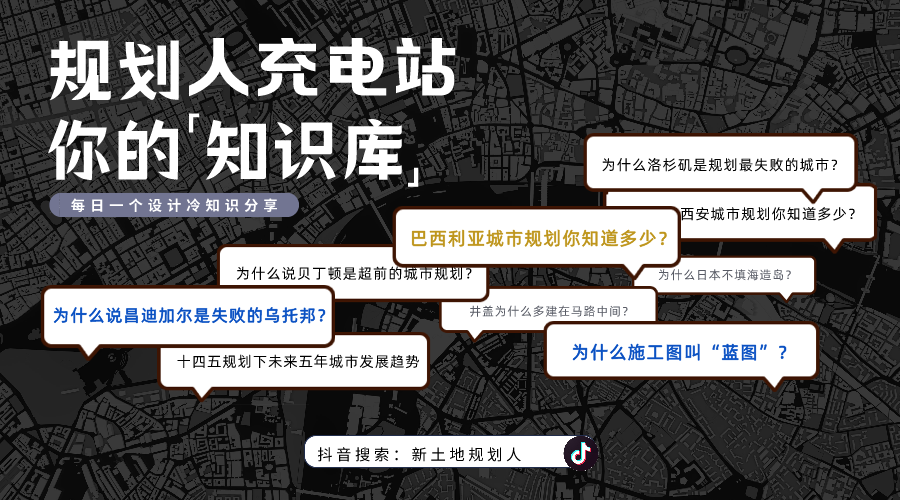
7月21日,李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一个星期后,7月28日何立峰副总理参与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连续国家领导层关注,一时间将城中村改造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么新时代的城中村改造应该怎么开展呢?按照何总理的话来说可以分为三类:拆除重建、综合整治、拆整结合。
本文结合过去城中村改造的经验,主要探讨拆除重建和综合整治两种模式,因为拆整结合就是拆除重建和综合整治的结合。理解了前两种模式,也就理解了拆整结合。


拆除重建模式
拆除重建模式涉及产权重置,要面向现状众多利益团体。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分配问题。因此,通过不同的利益分配方式又可以将这一模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引入开发商,增加容积率。通过增加容积率,给予开发商足够的利润、村民足够的赔偿,从而快速撬动城中村改造。这种模式在过去十多年在广东比较常见。优点是固投大、改造快、容易出政绩;缺点是对社会财富分配存在着巨大不公,让城市资产转移到了少数人身上,造成城市资产的流失。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看到,一个村拆迁造就多少个亿万富翁的新闻。例如深圳最大城中村白石洲拆迁,一夜间造就1878户亿万富翁。

如果说在增量中,城市最大资产是土地;那么在存量中,城市的最大资产就是容积。存量中的容积,就相当于增量中的土地。增量中的土地无法无限扩张,那么存量的容积也无法无限增加。城市化水平决定城市人口无法无限度增加,这就决定了人们需要的城市容积总量。过多建设的容积会导致供过于求,城市容积价值下降,让城市不断贬值。城市土地资源之所以能够那么宝贵,在于城市土地稀缺性。假设城市的土地能够无限供给,那么土地将一文不值。容积也是同样的道理,无限供给将导致价值下降。况且,容积的生成还受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承载力的约束。没有配套服务的容积等于垂直上的沙漠,除了探险和猎奇,没人愿意涉足。
另外一种是政府或国企下场,不大幅度增加容积率。这种模式做得比较好的是杭州的做地模式。其关键在于拆赔标准较为公平合理。与广东不同,杭州的征拆标准以人口为补偿标准,弱化“补砖头“的概念,强化宅基地的生活保障属性,不大幅度增加容积率,同时能够保障好村民的居住。这种方式在利益分配上没有将城市资产大规模转移到少数人上,而是通过收储再出让,回收大部分土地溢价。这也是广州想学习的做地模式。但是这种模式有很强的地域性,广东历经多年的市场化旧改,拆赔标准被推得很高的情况下,如何压下来是个几近无解的难题。
杭州安置政策鼓励“1+X”安置办法,即被补偿人选择1套安置房,其余安置面积均以货币方式进行补偿。货币化安置款根据货币化安置单价结合货币化安置面积扣除相应的调产安置用房结算价款后进行计算,即货币化安置款=货币化安置单价×货币化安置面积-相应的调产安置用房结算价款 。在安置时,选择区位较好的区域,优先完善学校、绿地、道路、公园等配套设施后,再进行搬迁安置,减少原权利主体的阻力。同时,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市人大[2014]24号),杭州市城中村拆除重建人均安置补偿不超过40平方米的标准。这就保障征拆成本,也避免了需要过度增容完成利益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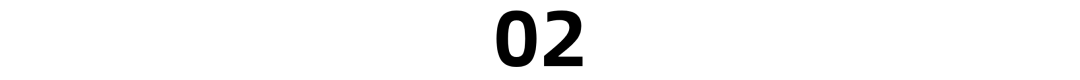

综合整治模式
综合整治模式核心涉及的问题是运营盈利问题。这种模式的利润极低,甚至很多都在亏本。但是由于城市化发展的需求,这种模式又很有必要。因为城中村不仅提供了廉价的居住空间、让很多外来客拥有落脚空间,而且大多城中村自身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生态,繁衍出独有的商业链、产业链,促进城市产业的孵化和发展。城中村的产业链小到可以维续一个家庭能够在一个特大超大城市中生存,大到能够孵化出一个个独角兽,甚至世界顶级企业,例如希音就是广州城中村农民工一针一线纺织出来的,华为、腾讯等等许多互联网科技企业都是从城中村走向世界的。
从综合整治的商业模式来分,可以分四种。
第一种是独立的整村综合整治。通过长租村民房屋,装修完善后,提高价格,统一租出去。这种典型代表是万科的万村计划。因为前期投入大,后期运营难以收回成本,这一模式宣告失败。

第二种是产业—廉价保障房的结合运营。代表案例是深圳水围村。虽然水围村在前期投入跟万科的万村计划模式一样,是亏本的,但是水围村只要保持运营阶段不亏本就能持续下去。因为水围村的房屋定位是定向给到特定企业,相当于企业的宿舍用房。也就是,政府投入一定金额对现有建筑改善,就实现了精准对位产业的保障房建设。这比政府单独在城市最核心地区划出一块地或者收储一块地,重新建设新的保障房便宜多了。从机会成本来看,政府在水围村这个模式中“挣大发”了。但是这种模式的运营会破坏原有城中村生态,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白芒村。

水围村(来源:网络)
此外,这种模式可以产生很多类型的分支,例如古城保护+综合整治运营。以南头古城为例。前期也需要政府输血完成整治,后期可以交给市场运营,只要保证运营阶段不亏,那么就可以实现古城保护与活化。这是公益类项目比较好的市场路径。

南头古城(来源:SEA)
第三种是发展壮大城中村原有的产业。典型代表就是大芬油画村和厦门曾厝垵。这两个村都是因为艺术出名,改造都采取综合整治方式,只是处理细节有一定差别,导致发展方向不太一样。
先说大芬村,一个驰名中外的油画村,油画卖到欧洲、美国。政府对其也是很珍惜,通过优化环境、改善市政管网(解决消防、卫生、安全问题)、修缮公共空间,甚至为其修建博物馆,使得原先的产业没有消失,租金没有变化,业态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反而不断发展壮大,甚至孵化出了好几个知名画师。

大芬村(来源:网络)
再说曾厝垵,临近海边,因为租金便宜住进了一群艺术家。后来艺术家出名了,把曾厝垵也带火了,于是很多人为了一睹艺术风采,纷纷跑来曾厝垵。曾厝垵租金也就水涨船高,艺术家因承受不起高租金而逃离了。但是借助厦门旅游城市优势,曾厝垵并没有因为艺术家的离开而衰落,而是在政府的整治下成为了文艺村、小吃村、旅游打卡热点。每每走进去都是人挤着人,好不热闹,这大概应该是全国最热闹的城中村了吧。

曾厝垵(来源:网络)
最后一种是历史文化名村。其处理方式更加丰富。对于一般的历史文化遗产处理方式有很多相关文章,已经做了很详尽的介绍,在此不赘述。这里主要介绍一种不需要政府输血,可以很好地解决产权以及活化问题的方案。那就是容积率转移,也可以理解为拆整结合模式。更客观地讲,这也是用容积价值换取的整治保护,更好的体现容积价值的神奇之处。
以湖贝旧村为例。湖贝统筹片区城市更新单元拆除范围30公顷,湖贝旧村1.4公顷。湖贝片区周边通过拆除重建进行改造,湖贝旧村则采取综合整治的方式进行活化。由开发主体出资赎回旧村的产权,并将其无偿移交政府。开主体可以获得旧村转移的容积(现状建筑面积的1.5倍),叠加在周边地块上,用“高楼包旧村”的方式推进拆除重建和综合整治的结合。


文章来源
X I SEA CiTY
编辑排版
中规建业城市规划设计院 信息中心
CONTACT US
合作/投稿/转载请联系
xjxtd@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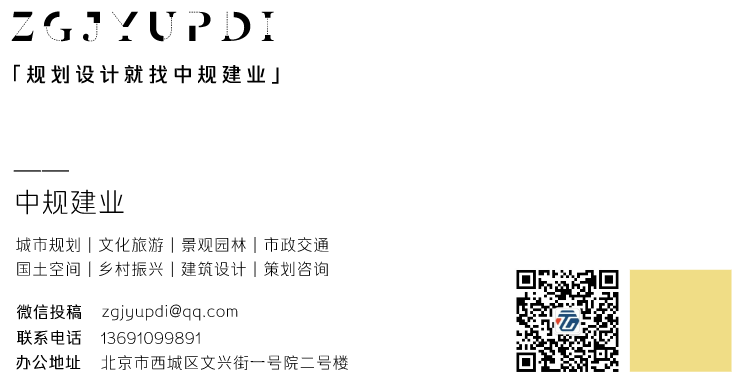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土地规划人):回顾 | “城中村”改造的死与生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