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自身存在人流密集、空间密闭、发生事故后救援难度大等特点,其运营安全问题一直是城市安全的重点关注对象。通过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特点、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事故案例、专家意见、相关理论研究的收集和分析,总结识别出城市轨道交通易发事故的危险源。利用风险概率-影响矩阵法,根据深圳市自身发展情况以及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的特点,识别出大客流拥挤踩踏、公共卫生安全、安保区结构被破坏、行车关键设备、自然灾害五种重要风险。针对事故风险点提出健全全过程风险管控体系、强化全方位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多平台智慧安全防控系统和优化维修计划四大运营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邓遥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研究背景
自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起,交通运输部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陆续出台了十余项关于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管理办法与技术标准,体现了国家和地方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高度重视。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已成为深圳市公共交通的骨干,随着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四期建设规划调整的批复和五期建设规划的推进,其线网规模仍将不断扩大,运营安全风险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加强运营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机制建设,多方面提高运营安全保障能力,防范和化解运营风险十分必要。
研究综述
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风险分析与评估需要依靠长期运营积累的经验、教训以及庞大的事故数据库。国外部分城市已经建立了以定量为主的风险分析评估模型,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运营风险评估体系。英国伦敦地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的特点和优势体现在工作的细则化,为了使评估的风险水平更加科学精准,其采用了定量风险评估(Quantitative Risk Analysis, QRA)、乘客风险评估(Customer Risk Assessment, CRA)以及工作场所风险评估(Workplace Risk Assessment, WRA)三种评估工具,覆盖了运营系统的全对象和全流程,便于管理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措施[1]。此外,英国及欧盟各城市还采用了统一的轨道交通事故(事件)统计指标(Common Safety Indicators, CSIs)和统一的安全统计报告[2],不仅可以对运营风险进行定量分析,还可以对不同城市、不同轨道交通系统进行多向对比,弥补安全漏洞,提高区域整体的运营安全水平。美国纽约地铁的风险评估体系采用的是安全风险认证报告(Safety and Security Certification, SSC)[3]。该报告相当于一份行动指南,规范了整个地铁运营系统中所有参与者的工作内容与流程,包括系统风险因素、安全风险指标的确定、检修与应急预案的实施、风险管控措施等内容。
2007年,原建设部颁布了《地铁运营安全评价标准》(GB/T 50438—2007),中国部分城市已按照其要求开展了地铁运营安全评价工作。由于缺乏大量的原始数据和事故案例,城市尚没有形成综合完善的地铁运营安全指标评价体系。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的路网运营安全风险评价体系[4]对指标和评价标准进行了量化,提出了设备设施隐患、车站客流风险、运营安全管理与保障风险三部分32个评价指标的千分制评价方法,有助于加强薄弱环节管理,促进系统化综合管控。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评价工作由市交通委员会组织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评价内容分为8个专业,流程是先分后总,先进行各子系统的评价,再进行运营安全总体评价,最后是对风险量化分级以及风险点分析和归类,提出整改建议。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特点
1)深圳市地质结构多样并伴随灾害性天气。
深圳市位于中国南部海滨,存在多处填海区,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较为复杂。部分区域存在断裂、软弱土层、花岗岩类残积土层、花岗岩球状风化、溶洞、地表水体以及具有腐蚀性的地下水。以目前正在填海形成的海洋新城片区为例,未来将规划多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经过,其建设运营存在挑战。
此外,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形结构以及海陆位置分布等因素的影响,台风、暴雨、洪涝成为深圳市主要的气象灾害。其中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危害最大的是每年台风季带来的狂风和强降雨。
2)随着新线的开通,客流激增,加大了网络化运营的复杂性。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自运营以来,客运量不断增长。2018年日均客运量538万人次·d-1,2019年5号线和9号线延长线开通后日均客运量冲击600万人次·d-1。部分车站客流已超过设计能力,早高峰小时部分区间超满载率的情况已成常态。截至2020年12月,城市轨道交通全网运营里程达411 km,车站283座。
随着四期建设规划的逐渐建成,至2025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650 km。随着新线陆续投入运营,人流管控、运营调度、设备维保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安全风险也同步增长,安全压力日益凸显。
3)枢纽站复杂的客流流线以及不同的建设时序,加大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组织的难度。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践行站城一体化发展理念,通过枢纽建设的契机,打造交通一体化、空间一体化的片区发展新节点。目前,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存在多处多线换乘枢纽,车公庙为四线换乘站,福民、福田、前海湾、深圳北等为三线换乘站,随着轨道交通网络密度的加大,枢纽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枢纽站由于线路、功能集聚,客流组成和流线较为复杂,在早晚高峰期,容易出现换乘客流流线冲突的情况。此外,枢纽不同线路的建设时序难以同步,若没有提前做好规划预留,新建线路可能会对既有线路的运营产生影响。
4)城市轨道交通一期线路关键设备开始老化,设备可靠性下降。
城市轨道交通一期线路运营时间已达16年,二期线路运营超过8年。一期工程接触网、承力索、轨道已进行了部分更换,至2020年250余辆列车进行了大架修。从现状运营情况来看,故障导致运营延误15 min以上的事件呈较快增长趋势,设备可靠性和稳定性下降,安全风险上升。特别是1号线信号系统故障较多,需要在沿线车站设备室安排专门的值守人员加强防范。
5)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建设开发速度快、密度大,安全保护区管理工作形势严峻。
在有限土地资源的约束下,通过轨道交通建设来引导、带动沿线片区的城市更新与重建,已成为深圳市推动城市转型、高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然而,随着沿线城市开发强度的加大,因外部施工作业侵入城市轨道交通安保区,破坏隧道、设施的情况时有发生,加大了轨道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难度。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评估
1
危险源辨识
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事故案例[5-6]、安全理论[7]和深圳市特点的分析,以及对相关者需求和专家意见的搜集,从人、机、环境、管理等方面,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全过程进行多维度排查,列举所识别的危险源,包括但不限于表1列出的类别。
表1 危险源分类

2
风险分析与评估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是指城市轨道交通在运营过程中发生某种安全事故(事件)的可能性及严重性的组合。结合深圳市近些年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事故数据以及专家意见,判断主要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影响等级,并运用风险概率-影响矩阵法(见表2)评判其风险程度,揭示出五大关键性风险:行车关键设备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为较大风险;大客流拥挤踩踏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和隧道、轨道、车站等安保区结构被破坏风险为一般风险(见表3)。
表2 风险概率-影响矩阵

表3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主要风险程度评估

1)大客流拥挤踩踏风险。
城市轨道交通是大运量交通工具,在高峰期、节假日等产生短时大客流甚至超大客流是固有的运输特性[8]。此外,封闭地下空间、高度密集人流,加上防疫社会形势导致的心理紧张,易引致拥挤踩踏风险。一是站内客流组织不当或短时站内超过安全容纳人数,在通道、扶梯、站台等部位引致拥挤踩踏。二是突发事件引致惊慌和羊群行为,如近年几起拥挤踩踏事件是由乘客自身不适晕倒引起周边乘客恐慌奔逃。
2019年,工作日早高峰(7:00—9:00)1,3,4,5,11号线局部区段满载率超过100%,最大达130%,个别列车局部区间乘客超过2 000人,最大达2 400人。深圳北站、车公庙站、老街站进出站客流和换乘客流总量达30万人次,坪洲、固戍、五和站等早高峰短时客流超过线路运能。
虽然2020年8月18日开通运营的6号线和10号线降低了部分线路的负荷强度,但1号线桃园—深大区间、3号线水贝—草埔区间、4号线民乐—上梅林区间、11号线宝安—前海湾区间的高峰小时线路满载率仍大于100%,存在大客流拥挤踩踏风险。
2)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深圳市作为中国典型的移民城市在这次疫情中也面临严峻挑战。城市轨道交通作为深圳市公共交通的骨干力量,是公共交通系统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之一。在重大疫情面前,城市轨道交通承担着保障出行需求和防控疫情的双重责任。
对于新冠肺炎这类传播性强的疾病,防控要求将患者隔离,将不同风险等级人群分离,减少人员接触。但城市轨道交通自身的空间狭小、密度高、大客流等特点与防控要求矛盾,容易引发疫情传播、交叉感染等问题。此外,新冠肺炎患者在前期可能存在并无明显症状但具备传染性的情况,仅依靠车站出入口的体温检测设备难以识别无症状患者。当患者或疑似患者进入车厢后,可能导致整个车厢甚至整个车辆的人员变为有接触史的密切接触者。由于乘客位置难以定位、流动性大、排查基数大,导致接触人员追踪困难,且多存在滞后性,容易造成接触人群呈指数增长。例如,2020年1月22日,一例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乘坐了青岛地铁,且期间换乘了多条线路,运营公司耗时2天才完成排查,最后导致数十名乘客受影响需居家隔离观察,相关列车下线进行全面消杀。
3)隧道、轨道、车站等安保区结构被破坏风险。
安保区被破坏存在内因和外因两种情况,均可能导致运营中断或人员伤亡。外因可能存在的情况有:周边开发引发水土流失导致隧道塌陷;部分施工作业(特别是勘探阶段)不按规定申报;违法施工导致隧道被打穿等。
内因可能存在的情况有:施工质量不过关或渗漏水等导致隧道发生沉降;由于枢纽站各线路建设时序不同,在上跨或是下穿运营线路时,若施工不当,容易对已运营车站造成影响。例如,隧道掘进过程中可能存在局部地段切断地下水的径流,造成地下水的流失或是导致水体倒灌隧道;已运营车站周边多存在大量管线,若施工不当引起地表沉降或者盾构引起地表隆起将导致既有管线周围土体变化,危害管线安全。以在建的黄木岗枢纽为例,7号线(运营)、14号线(在建)和24号线(规划)在该枢纽交汇,节点复杂,且需改造既有7号线,并与上方新建的道路隧道结合,容易给既有7号线车站和旧路衔接段带来风险。
4)行车关键设备风险。
行车关键设备如信号系统、通信系统、车辆系统均按照“故障导向安全”的原则设计,信号自动保护系统及车辆自身保护系统能有效保障列车的安全运行。但在新线开通密集或是设备使用一定年限,进行设备更换、升级或系统改造、更新后,可能会存在调试不充分、新旧设备不兼容、预设条件冲突等情况,产生列车冲突、脱轨等风险。例如,2019年3月18日,香港地铁荃湾线在进行新信号系统测试时,对向的两辆列车发生了擦撞。
深圳市2020年共开通了7条城市轨道交通线段,包括2号线东延、3号线南延、4号线北延、6号线(一、二期)、10号线以及8号线一期,全长共计107 km。由于新线开通密集,新设施设备投入运营初期调试、磨合概率高,可能会出现设备故障问题。
此外,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以及《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6—2035)》,未来将有多条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经过前海合作区,由于道路条件限制,对于梦海大道等需求较大、条件较好的通道,可能会考虑采用共线运营的方式。但此做法需要在规划阶段对区域内的城际铁路线和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进行统筹考虑,保障车辆制式统一,解决信号系统兼容等问题,降低行车关键设备风险发生的概率。
5)自然灾害风险。
台风是深圳市发生最多、危害最大的灾害性天气。台风季为每年7—9月,通常会带来强风和强降雨。近年来,台风天气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例如,发生雨水倒灌车站、高架段/全线路停运导致乘客滞留等情况。
对于高架线路,例如6号线、11号线碧头站—机场站区段,还可能发生外部异物被强风吹入限界、车辆脱轨、设备设施遭受雷击等情况。此外,规划的8号线二期将延伸至海边的大小梅沙,需谨防台风导致海水倒灌线路和车站的情况。
运营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1
建立运营单位提前介入机制,健全全过程风险管控体系
在城市轨道交通前期的规划、设计、建设过程中需对后续的运营服务需求作出充分考虑。为加强前期工作与后期运营的有效衔接,原则上应当在新建线路可研报告编制前确定运营单位[9],保障运营单位人员的全过程参与,从而在规划、设计、建设阶段为各相关单位提供关于空间、设备在管理、维护与长期运营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例如,对安检空间的提前规划设计,可以减少因设施设备占用人流空间产生大客流拥挤踩踏的风险。
此外,运营公司人才的提前进驻,加强了对施工的监督,提升了工程质量,使建筑体与设施更加完备,减少问题产生的可能性。运营公司的提早介入,可以让轨道交通运营中的诸多风险在前期得到控制,形成全过程的风险管控体系。
2
强化全方位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应急能力
一是完善事故信息发布制度,建立应急短信发送平台[10],便于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减少恐慌,同时对乘客的行动进行引导和疏散,避免衍生事故的发生。为了提高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效率,需要对工作内容和流程制定标准和细则,明确信息发布的主体、途径、内容等。
二是健全应急组织机构,推动应急联动体制,形成“多方联动,逐级上报”的应急响应机制。竖向形成“深圳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机构—地铁集团/参建单位—车站”的三级组织模式,横向形成运营公司、建设单位、政府相关部门、辖区政府、市公安机关、公交、电力、通信、供水等单位[11]的联动组织模式,加快对信息报送、人员疏散、设施设备抢修等关键环节的响应,提高协同应对事故的能力。
三是完善应急预案体系。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在运营过程中的大客流拥挤踩踏事件、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爆炸、自然灾害以及突发性设备故障等原因造成的运营危害,制定相应预案,明确不同级别安全事故的上报层级与联动部门和单位,形成“一类一预案”的应急预案体系。
四是强化安全演习。除了城市轨道交通相关单位内部的应急演练外,需至少每年公开组织一场应急演练,例如对火灾、列车冲突、脱轨等事故的模拟演练,加强市民的安全意识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
3
拓展多平台智慧安全防控系统
1)气象专用信息服务平台应对自然环境影响。
与深圳市气象服务中心合作,在高架线路、地势低洼以及沿海的车站沿线设置气象监测自动站,自动将该区段的风向、风力、降雨量、雷暴情况等核心信息报送到轨道交通控制中心。当达到维持运营能力上限值时,系统能够实现自动报警,以便运营公司迅速采取应急措施。
2)智慧疾控联动平台降低传染风险。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已逐步实现“扫码过闸”“二维码上传同乘信息”等实名乘车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实名追踪的能力。应充分利用GPS定位、5G通信、生物识别、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实现乘客信息的快速录入、精准查询、同步更新。并联合卫健委、疾控中心,构建有效的疫情预测预警排查系统,及时预警,减少安检员等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形成科学精准追踪的疫情防控系统,进一步提高流行性传染病疫情应急管理能力和决策指挥效率。
3)大客流监测平台预防踩踏事故。
增加基于视频识别的客流密度监控预警系统,对城市轨道交通内客流量、排队长度、区域客流密度进行实时监控,并通过提前计算出各区域的最大客流承载能力来判断存在大客流安全隐患的节点,从而进行预警,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精准地采取引导、疏散措施,避免事故发生。
4
优化维修计划,增加状态性检修
城市轨道交通采用相对固定的计划维修模式,对设施设备的故障状态难以精准及时处理。将设备的检修模式由计划检修逐步转变为状态性检修,能够更及时地发现安全隐患,减少因设备突然故障对行车造成的影响,同时还能对故障部位进行针对性的检修,缩短其下线检修的时间,以便快速恢复运营,减少人力和资源的浪费。
目前,在建的城市轨道交通20,12,13,14和16号线的列车均配备了全自动运行系统,为采用状态性检修提供了良好条件。通过列车的信息和自我诊断系统,对车辆部分机械、电气系统进行检测,当发现磨损超过极限值或是故障时,车辆将自动对异常情况进行记录和评估,并反馈给中控系统。
结语
本文采用风险概率-影响矩阵法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要风险进行了评估,识别出五大重要风险。其中行车关键设备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为较大风险,大客流拥挤踩踏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和隧道、轨道、车站等安保区结构被破坏风险为一般风险。针对识别出的风险提出了健全全过程风险管控体系、强化全方位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多平台智慧安全防控系统和优化维修计划四大运营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城市交通》2021年第5期刊载文章
作者:邓遥,欧阳新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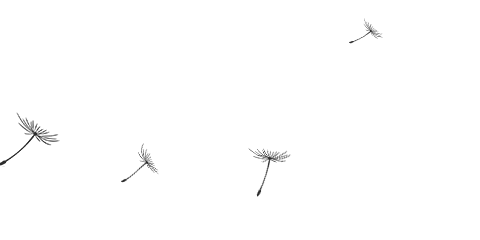
封面图片来源:
《城市交通》自选图库
拍摄:杨晓娥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案例研究”栏目更多内容
关注解锁更多精彩
2022024期
编辑 | 张斯阳 耿雪
审校 | 耿雪
排版 | 张斯阳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交通):邓遥 |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析及管控措施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